996当然违法
马 宁
2020年,中国实现了两个壮举: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上首次消灭绝对贫困,另一个是实现了十八大关于“收入倍增”的计划,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两件大事的本质,说到底都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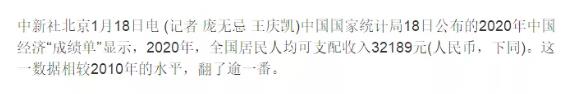
如果只看GDP名义增速,比如在非洲,这些年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在5%-6%左右,和中国相差不大。印度有几年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中国。但是说到10年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中国独有的成绩。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再快,居民人均收入也增长得很慢。甚至因为分配的极端不公平,经济越增长,社会矛盾越突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比如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四月革命之前的阿富汗,看起来欣欣向荣,超短裙摇滚乐,却会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这也是为什么境内外一直有人唱衰中国的原因。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在唱衰中国方面,最著名的就是那个章家敦,说了二十年中国即将崩溃。论铁饭碗,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章家敦,知道有人最爱听这个就说了二十年这个,常说常新;另一个是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陶伯特,为了几页纸怎么编排从60年代一直吃到死。
任何变化都是有原因的,不存在形式主义的规律。一个社会从繁荣中倒下,除了外力作用,基本上都是由于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不论怎么吹嘘“企业家”们的贡献、怎样贬低劳动者的价值,阶级斗争不是大专辩论赛,不是谁说得天花乱坠谁就赢了。
中国之所以能稳定发展,关键就在于大多数普通群众分享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这一点之所以能够实现,当然不是依靠所谓的市场,靠的是国家的规划。市场的分配方式,好听一些的说法,是“按要素分配”;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就是划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至于剩余劳动,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劳动的那些人各自瓜分。如果按照市场的分配方式,显然不会有什么公平和普惠。因此,市场虽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在分配稳定方面就差远了。
最显而易见的,我们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但在单纯的市场分配下,体现的更多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资本所有者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劳动者远无法与之相比。每年胡润富豪榜单的财富数字都漂漂亮亮,一年比一年高,每一个互联网巨头上市都能造就一大票的千万亿万富翁。
靠这些资本和富翁搞稳定分配和共同富裕显然是不可能的。为稳定分配做出贡献的,还是那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虽然政府这只手经常在资方和劳动者之间摇摆,但总体上还是充当了社会缓冲器的角色,平衡了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本文一开头提到的2020年实现的两个壮举,就要归功于这只手。
这只手最大的问题,在于既然要充当社会缓冲器,就天然的有和稀泥的倾向。本来,劳动者并不奢望有特殊的照顾,做到以法律为准绳即可。可是在事实上,这个缓冲器总是要考虑很多问题,为了经济发展,不能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要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又要维护好社会稳定。近期,人社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明确“996”违法。这是好事。不过“996”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很多事情劳动者莫名其妙吃了亏。甚至在2019年还有个“996ICU”的著名事件,还有那个著名的引起轩然大波的“福报”事件。按照我国《劳动法》,“996”是明明白白的违法,现在还要通过人社部和高院联合用典型案例的形式来定性违法,可想见之前的阻力。

万幸,至少在社会产品分配这个问题上,这只“看得见的手”虽然犯了很多错,但总算还是没有忘记它该扮演的角色。二十年来,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虽然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飞扬跋扈的富豪倒下去了,不论他是不是“人民富豪”,这两年反垄断和各领域对资本的遏制政策也在密集出台。
最近伴随国内对滴滴等互联网企业的整顿,对教育行业资本的治理,国外舆论开始渲染一种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认为国内对资本非常不友好,这将会引发资本逃离中国。
随后,在8月17号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在这之后,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始表态愿意拿出多少多少钱投入到社会项目中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等等。这又被一些声音认为是要杀富济贫。就在人社部和最高法通报“996”违法的同一天,相关部门出来说“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可以理解这是为了平息恐慌性声音,稳定市场。但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根本还轮不到“杀富济贫”的阶段。劳动者所求的是按劳动法规保障自己的收益和权益,如果企业家把这种要求理解为“杀富济贫”,那只能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识还不够清醒。
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沉思录之前的文《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解释了相关概念,也分析了一些具体可能的机制。原本的定义指社会慈善领域,但在当前语境下这个定义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三次分配指的是社会企业提供公共品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分配。当然,不管原本的概念还是现在的概念,它只能是一种补充。
比如从原来的慈善概念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其中,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1140.46亿元。可以做一个对比,2019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20854亿元。这样一比较,慈善事业有点像开玩笑了。当然了,也许是个很有前途的玩笑。
从现在的私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看,像近期的比如各大互联网巨头提出要拿出多少钱投入到社会项目中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等等,很多人觉得他们掏这么多钱,直呼善人。实际上参照互联网企业过往的经验看,虽然我们看到互联网企业经常巨额亏损,但那都是恶性竞争弄出来的,他们一般开始做项目的时候起码不会做一个模型上就亏钱的项目,尤其这些年B端和公共端的项目都是比较稳定的利润点,而且互联网领域往往都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玩法。另外,过往国内这些互联网企业也都宣称和参与过不少社会项目,但实际投入力度和效果很难说,比如沉思录之前的文章《阿里巴巴,路走窄了》中就提到过阿里参与的一个云南扶贫项目中的坑爹情况。所以,这些东西没落实之前,我们很难去评价,而且从总量上来说,可能会比慈善规模大,但也难以影响大局,完全无法与国有经济主导的二次分配相提并论。

共同富裕的重点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靠减少低收入群体来实现的。如何减少低收入群体呢?一是利用税收等方式调节高收入,二是利用社保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低收入。究其根本,还是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显而易见,现在政府,社会和民众要求垄断企业,金融资本,平台经济等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求它们要额外付出,而恰恰是它们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严重缺失。比如社会转嫁成本问题,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对公众数字劳动无偿占有并进行垄断经营获利问题,996和外卖员保障权益缺失问题,金融资本乱象问题等等。指望它们自愿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法律,政策和税收来解决。
所以,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制度,就是中央财经会议精神所说的那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三次分配,一个也不能少。初次分配是主体,再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只能是一个补充。
PS:后面我们会再聊聊税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