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社会权力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段学慧
摘要:资本表面上看是一种生产要素,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资本的所有权这一根本权力必然孳生出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在内的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权力。因此,权力是资本的基本属性。资本社会权力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资本赖以产生的生产关系。从历史逻辑来看,资本社会权力是由商品的社会权力演化而来的,但最终必然被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社会公共权力所取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面临着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历史任务,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驾驭资本,把握不同资本的行为特征,促进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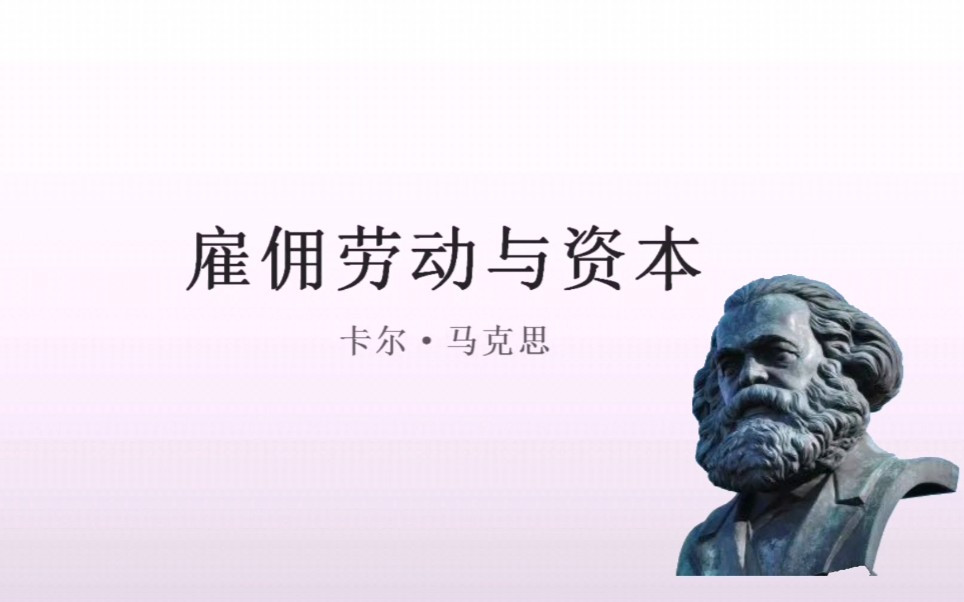
一、问题缘起
关于“资本的社会权力”,马克思最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指出它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1]726,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描述为“一种社会力量”[2]4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3]217。然而,学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社会权力的研究并不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大量的研究是为“资本扩张”提供学理依据和对策。进入21世纪以后,个别学者开始注意到资本扩张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危害性的关注。自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4]218,“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4]211,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4]217自此,关于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的研究才得到较多的关注。学者们把资本权力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区分开来的关键,认为资本权力根源于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5]或资本对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人类物质劳动的掌控;[6]资本权力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与方式;[7]资本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三种形式;[8]只要资本作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再生出来,资本的权力就必然地再生出来;[6]资本权力扩张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从而实现人类解放,[8]只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取消资本权力对劳动的统治才能超越资本权力的逻辑。[9]上述这些研究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并丰富了马克思的资本社会权力理论。但是,对资本社会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容的研究还比较笼统,比如资本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究竟是怎样阐述的?目前学界虽有论述,但还属于片段性的,缺乏系统性;其次,大多研究仅从“资本权力”本身来研究,没有看到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最后,把资本社会权力的生成逻辑归因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属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只是说明了资本权力生成的社会根源,但从唯物史观的视野来看,要把资本社会权力的历史逻辑说清楚,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近期围绕“资本无序扩张”的研究来看,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一种生产关系,对资本社会权力属性的研究重视不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形式上是一种生产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社会权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虽然其中没有一个篇章以“资本的社会权力”为题,但却始终贯穿着对资本社会权力的论述。
综上所述,鉴于学界的研究现状和党中央对资本问题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主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蓝本,系统梳理和挖掘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论述,重点归纳和提炼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社会权力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深入探究资本社会权力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所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从中汲取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启示。

二、资本社会权力的内容
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是马克思的一个抽象的、总的表述。要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社会权力属性,必须首先明确资本的社会权力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和形式。
1.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0]31,32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生动地刻画了资本的经济权力。
(1)资本是一种所有权——资本的根本权力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首先体现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资本必然对劳动的主观条件拥有实质上的所有权。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所有权,他出卖的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这似乎是一个基本常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劳动力的买和卖”一节中所指出的:“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11]195,196然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只是简单流通领域的表面现象。“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1]205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与劳动力的买卖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力的所有权及自主权,等待他的将是资本家行使像任意处置自己的物品一样的所有者权利。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权,而实际上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充裕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当“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性法律来实现它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11]662马克思举例说在1815年以前,英国禁止机器工人移居国外,违者予以严惩;还有,美国南北战争导致欧洲棉荒和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失业,于是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呼吁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可是英国的棉纺织厂主却反对把失业工人转移出去。马克思随后写道:“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11]662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3]429建立在资本所有权这一根本权力之上,资本自然就拥有了支配劳动的一切权力。
(2)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权——资本的核心经济权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意识到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然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对一般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1]611剩余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成为无酬劳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剩余劳动就转化为剩余价值。
资本获得剩余价值是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3]994然而,“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11]674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具有经济强制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成为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手段。
资本不仅在生产领域占有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在流通领域占有商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实现的剩余价值。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不仅表现为占有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还表现为各种资本要求平等地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所以,在平均利润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3]217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农业资本等各种资本都要求分割社会的总剩余价值,从而形成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当虚拟资本出现以后,虚拟资本也要求分割未来的剩余价值,或者通过对未来剩余价值的贴现,分割现有的剩余价值。[1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当时出现的股票、国家债券、银行空头汇票等几种虚拟资本怎样凭借资本所有权分割剩余价值。可见,资本形态的历史演变,不会削弱资本反而会增强资本的经济权力。
(3)资本对劳动的指挥权、监督权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指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13],“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11]216,“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11]359
资本的指挥和监督权是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对抗性质所决定的。“指挥和监督的劳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433“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11]385
随着分工协作的不断发展,“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样;“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实际承担指挥和监督职能的是“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11]384,385
(4)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3]927,实质上是具有间接性、隐蔽性的强制劳动。就资本未付等价物而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来看,“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159“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11]359
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表现为对在业工人采取大大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在正常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工作带回家去完成而实际上支付低于市场价格的报酬等强制过度劳动方式;对那些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受救济者、游荡和行乞的人,往往被收容或管制起来进行强制劳动而不支付报酬。当机器出现后,机器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反而把“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妇女和儿童也纳入强制劳动的队伍,“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11]453,454
资本的强制劳动,不同于奴隶制直接的、赤裸裸的、超经济的强制劳动,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所决定的经济性的强制,是资本逻辑强加给工人的。“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11]360并且“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1]359
(5)资本对劳动力的任意使用权和解雇权
“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11]271尽管机器大工业为缩短劳动时间创造了条件,却“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1]469,使得“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1]487,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
资本不仅拥有任意使用劳动力的权力,而且拥有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11]636为了减少用工成本,雇主们经常用解雇威胁家长,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当儿童“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12]558;当采用新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的工资总额时,资本家就会毫不留情地解雇工人。因而机器每改良一次,都会有一部分工人被解雇;当某种商品在较大范围内持续较长时间市场价格趋于下降时,生产这些商品的雇用工人就会被解雇;经济危机时期,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都会遭到资本的解雇。
资本还把解雇工人作为压制工人运动的手段。例如,“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11]292当煤矿井下工作面空气不足时,“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1]574“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11]768总之,资本对工人的任意解雇权服从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
综上所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权、对雇佣劳动的指挥权和监督权、强制劳动权以及任意使用和随意解雇工人的权力等,都是资本所有权所衍生出来的权力,实质上都是围绕支配无酬劳动展开的经济权力。
2.资本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14]为了满足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资本并不满足于经济权力,而是谋求政治权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1)资本权力与国家权力
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是资本权力的集中体现。然而,资本权力上升为国家权力或国家意志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资本在萌芽时期,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不足以吮吸足够多的剩余劳动,还需要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帮助。马克思指出:“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11]847马克思以英国1349年爱德华三世时的劳工法和法国1350年颁布的敕令为例,说明早期的劳工法就是资本求助于国家权力的结果:它们都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雇主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工人则要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还有英国17世纪末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1]861
随着资本权力的不断扩张,国家权力完全变成了资本权力的奴仆。马克思在阐述资本积累时讽刺道:“18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11]832
资本和国家权力往往相互勾结、相互渗透。资本通过收买官员或跻身国家权力机构,使国家权力为之所用,之所谓“资本权力化”;拥有国家权力的官员也与资本联合为个人谋利,之所谓“权力资本化”。马克思举例说,为了反对工厂法关于给生产设备安装安全设施的法律规定,工厂主成立了包括治安法官在内的“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而其中的治安法官大多数是工厂主或工厂主的朋友,还有一些工程师以专家的身份尽力替工厂主进行辩护。[3]104,105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15]
当资本权力的扩张危及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时,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也会制约资本权力,比如现代工厂法对工作日和使用童工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资本权力的限制或干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总之,不管是资本发展的早期依附于国家权力,还是资本壮大后拥有国家权力,资本始终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支持,国家权力作为资本权力的总代表,始终维护资本的权力。
(2)资本的阶级统治权
资产阶级从封建主阶级手里夺取政治权力以后,资产阶级便利用这个权力使曾与他们一起反封建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权源自资本的经济权力,即“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11]84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强调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单纯从分配关系和收入来源来解释阶级的差别,“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3]894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变得更加容易。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对手工劳动的分解和工具的专门化,以工人技能的畸形化使劳动隶属于资本,从而“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11]422。机器大工业以后,“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而且“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力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11]501
通常情况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支配的,即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支配的。在特殊时期,比如工人罢工影响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运用“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即运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比如,1867年2月比利时矿工罢工就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11]693。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作日的缩短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表面上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实质上是为了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3.资本的文化权力
资本的文化权力主要体现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550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他们在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必然把他们的思想观念或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资本逻辑的观念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之上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资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表现为资产阶级表面上极力宣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背后又通过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排除不符合资本观念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阐述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阶级性,指出“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1]43,同时也指出新闻出版自由应当是人民普遍享有的权利,而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的特权。针对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马克思于1842年1月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立法,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对进步文章的查禁,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得以发表。1842年1月1日创刊的《莱茵报》,由于日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于1843年4月1日起被普鲁士政府查封。1851年,海·贝克尔(Hermann Becker)开始在科伦出版马克思文集,但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查禁,该文集在第一版出版后即被禁止。《资本论》在出版时就受到了来自资本势力的反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17足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资本的平等,只不过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平等。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做自己的天赋人权”[11]457,“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11]338比如,由于工厂法限制资本对儿童劳动的剥削,工厂主为了防止别的工厂违规使用童工而获得更多利润,呼吁法律严禁一切部门违规使用童工,“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11]564所谓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也不过是资本瓜分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力的平等,是资本家之间的平等,而不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平等。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是没有丝毫人权的。“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11]3061844年的法令规定不允许雇佣11岁以下的儿童,同时允许雇佣11-13岁的儿童每天工作10小时,这就意味着取消了儿童本来可以受到的教育。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随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在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的未来教育的幼芽,但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出发点是为资本赚钱服务,而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再拿选举权来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开始就被剥夺了选举权,后来在工人阶级不断进行工人运动和议会斗争后,才争取到了少数席位的选举权。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其民主权利也取决于资本的数量多少与实力大小,大资本排挤、压榨和统治小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16]
可见,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资本的特权,归根到底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话语体系。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特权包装为天赋人权,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代替具体的资产阶级的特权。
以上对马克思资本社会权力内容的梳理表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是以资本所有权这一根本权力为基础而孳生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力在内的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权力。因此,也可以说,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权力是资本的基本属性。只要资本存在,资本权力就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资本的权力也一同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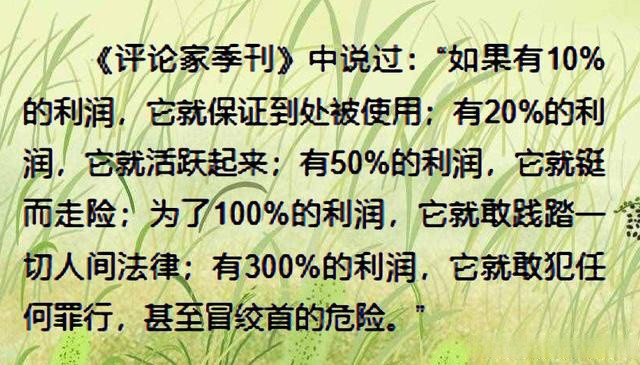
三、资本社会权力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趋势
1.资本社会权力的历史渊源——资本的社会权力是从商品的社会权力演化而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述了资本的社会权力是怎样从商品的社会权力演化而来的。
首先,商品的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商品自己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11]61,一方让渡使用价值从而获得价值,另一方让渡价值获得使用价值。“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11]187而商品的权力来自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生产关系的“价值”,这是商品所有者行使商品权力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商品的社会权力转化为货币的社会权力。在商品交换长期发展过程中,价值形式经过漫长的演变最终以货币形式作为它的完成形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商品社会“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11]156,商品的社会权力就转化为货币的社会权力,即“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0]52人们既可以手握这个“物的神经”或“社会的抵押品”购买任何商品,也可以把它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贮藏起来。[11]154这样,货币所有者就可以“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因为“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0]51。“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11]154
最后,货币的社会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社会权力。在资本运动G—W—G’中,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商品权力怎样转化为资本权力: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11]180这里的商品,不仅包括作为物的商品,更重要的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资本就拥有了对劳动的支配权、监督权、指挥权等一系列权力。
总之,从历史渊源来看,资本的社会权力是从商品的社会权力演化而来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商品的权力就转化为货币的权力;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的权力就转化为资本的权力。资本的社会权力最终来源于生产价值的社会劳动。
2.资本社会权力的社会根源是资本赖以产生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3]894这个“最隐蔽的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础”就是生产关系。资本的社会权力是由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的先决条件,起源于各该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17]资本的经济关系性质决定了它不仅支配整个经济活动,而且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一切社会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
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行使的各种支配权不是由其纯粹个人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其作为生产关系的支配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11]386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首先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但是资本作为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力不能仅从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去解释,而是要从资本所代表的根本经济关系中去解释,即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要素的所有权或产权。所有权反映在资本主义法律关系上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衍生出资本在一切领域的统治权,即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
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社会权力的分析,不是纯粹就资本权力本身来论述资本权力,而是建立在“物”的或经济关系的逻辑上,即资本社会权力是以“物”为媒介的建立在人对物的支配权力基础上的人对人的支配权力,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而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仅仅理解为“物的关系”,“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18]马克思正是找到了资本社会权力的“最隐蔽的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础”,才使得资本社会权力理论有了深厚的基础。
3.资本社会权力的发展趋势——资本社会权力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社会权力消灭了封建等级特权,以高度社会化的形式履行所有权、监督权、指挥权等支配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资本社会权力代替封建特权,实质上是以一种特权代替另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决定了资本社会权力不是永恒的,它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首先,资本作为普遍的社会权力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具有资本的一切属性和权力,但是资本不是资本家创造的,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仅可变资本是工人创造的,而且整个资本都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工人为资本家创造了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剥削剩余劳动不是一个资本家的特权,而是整个资本家的特权。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一种权力——不断出卖劳动力的权力。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工人受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就不会改变。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生产条件与工人的分离也不断加剧,工人不仅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而且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其结果必然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资本的这种普遍的社会权力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外壳必然要被“炸毁”,剥夺者必然被剥夺。
其次,资本的一般社会权力与资本家的私人权力相矛盾。资本的一般社会权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落实到产权上使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具有私人的性质。资本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所拥有的私人权力受追求剩余价值的驱使,必然产生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生产条件日益成为公共的、社会的条件,“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3]293,294这一矛盾“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3]294劳动者共同拥有和支配的公共社会权力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终将代替由榨取劳动者剩余劳动堆砌而成的资本的社会权力,这正是资本权力无限扩张与自我扬弃的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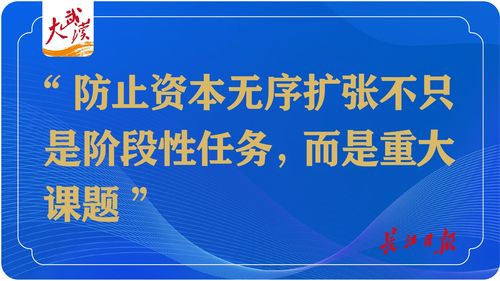
四、马克思资本社会权力理论的当代价值
虽然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社会权力问题,但是其中蕴含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和资本社会权力的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等,对我国当前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面临着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历史任务
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公共社会权力取代资本的社会权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首先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科学推论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差距。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为最终消灭资本、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资本的存在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社会权力的生成逻辑表明,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商品的社会权力进而货币的社会权力必然转化为资本的社会权力。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4]218不管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具有资本的权力属性,必然存在资本的权力扩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构成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更应当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2.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驾驭资本权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统治一切的权力。但是,“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1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资本权力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让“资本权力”上升为“一种社会权力”。资本发挥作用必须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范围内发挥作用。[20]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驾驭资本权力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处理好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关系的根本遵循,坚持“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21]是驾驭资本权力的制度底线。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资本权力扩张才能在总体上可控。要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发挥公有资本“普照的光”的作用,引导非公有资本健康发展。[22]
坚持党的领导,是驾驭资本权力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资本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给资本设置“红绿灯”是驾驭资本权力的法律保证。要研究各类资本权力扩张的规律,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法律,不给资本权力扩张留下法律和制度漏洞,依法加强对各类资本的监管,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3.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既要驾驭资本,也要制衡权力
对资本社会权力的分析表明,资本无序扩张实质上是资本权力扩张,而资本权力扩张主要通过“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两种相互交织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有一个时期我们重视了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资本权力扩张的消极作用,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把公权资本化,与私营企业主勾连、寻租等腐败行为频发;有的资本大鳄混迹政界谋取政策利益;有的私营企业主为了寻利贿赂官员、围猎党的干部。资本权力化是资本异化的结果,权力资本化是权力异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资本权力化还是权力资本化都是符合私有资本逻辑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化违背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初衷;而权力资本化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仅要驾驭资本,而且要制衡权力:一方面要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另一方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3],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构建资本和权力的“亲清”政商关系。
4.区分并把握各类资本的不同性质和行为特征,分类驾驭资本权力
目前存在的各种资本按照所有制性质可以分为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私有资本)两大类。它们都有资本的共性,即生产要素属性和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24],以及权力扩张的内在驱动。但是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其所存在的资本权力风险也不同。
公有资本是公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形式,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公有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不是雇佣劳动关系,利润目标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目标,还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本产权所形成的行政代理和经济代理相互交织的委托代理关系,本身就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为“公有资本权力化”埋下了伏笔。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以权谋私、国有资产流失、忽视职工权益等现象正是公有资本权力化的表现。把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反腐败斗争和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是规范国有资本权力的当务之急。目前,大多数农村缺乏集体资本经营意识,缺少集体资本经营人才,没有发挥出集体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需要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来发挥集体资本的作用。
非公有资本或私有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其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劳资之间是雇佣劳动关系。但是,非公有资本和非公经济人士中不乏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比如清末民初实业救国的爱国企业家张謇,近代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和银行家庄世平,当代以科技强国为己任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等,他们是非公有资本的典范。但也有一些非公有资本偏离国家政策目标、刻意逃避监管,有的利用平台优势搞不正当竞争,有的甘愿充当外国买办资本,金融领域出现的违规出资、关联交易、高杠杆、与境外资本勾连等无序扩张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当然,目前大多数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是守法规范经营的,这类非公有资本是需要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对象。
当前要特别警惕和防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野蛮扩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25]其权力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资本的社会权力俨然已经演变为资本的世界权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恶意收购我国民族企业、垄断我国竞争性产业,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等扰乱我国经济秩序;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断输入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制造历史虚无主义;在军事上频频在我国周边寻衅滋事、挑起争端。为此,我们要构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屏障,防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权力扩张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干扰。
5.驾驭数字资本权力,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联姻形成了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是投放在数字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资本,它是通过对数字技术和数据的垄断,借助数字平台对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的一种资本形式。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以金融资本为基础,是金融资本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兴起和繁荣。[26]因此,数字资本的基因是资本,实质上依然是金融资本,是数字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变种。
数字资本继承了资本的权力扩张属性,借助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其扩张能力和速度远超过以往任何一种资本形式,其控制力不仅限于生产领域,而且社会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意识形态无不打上数字资本的烙印。数字资本一方面加剧失业,另一方面使从业者劳动强度成倍上升;其平台化、去雇主化的就业模式,成为资本推卸工人福利责任的一种新发明;数字资本垄断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加剧两极分化;数字资本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行使数字霸权,网络战、信息战、舆论战都是数字资本主导的新型战争模式,甚至现代直接的军事冲突中都有数字资本权力的操纵。
随着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一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野蛮生长、缺乏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4]302为此,只有将数字资本主导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公有数字资本占主体地位,才能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才能防止西方数字垄断资本扩张和私人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5]许欣驰,薛忠义.马克思透视资本的三重论域:财富、权力、环境[J].学术探索,2022(10):60-65.
[6]刘志洪.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及其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2):148-158+238-239.
[7]于天宇.作为资本增殖的权力增殖——资本主义社会主体自我实现的“隐形屏障”[J].南京社会科学,2022(7):23-31.
[8]苗贵山,张雪薇.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研究[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34.
[9]薛绍文.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双重进路及其超越——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J].学理论,2022(11):22-26.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鲁品越.走向深层的思想:从生成论哲学到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0.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6.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0.
[19]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4.
[20]江宇.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11):47-50.
[21]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N].人民日报,2015-11-25(001).
[22]周绍东.“普照的光”如何发挥作用?——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3):19-27.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81.
[24]段学慧,刘丹.剩余价值二重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J].海派经济学,2017(2):22-36.
[25]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49-65+159-160.
[26]蔡万焕.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当前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新动向[J].山东社会科学,2022(6):124-130.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