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版福贵想起余华的“毛泽东会很生气”
秦 明
上个月18日,谭sir在B站粉丝数破百万,谭sir放出了一则自己十年前摄制的老视频作为“粉丝福利”,也算是对自己初心的表白吧。

父母没了
老婆孩子没了
哥哥也没了
只有自己和弟弟
还有一条狗
弟弟还有智力障碍
……
视频中,蹬三轮车的老大爷的悲惨经历看哭了无数网友,称这是“现实版本的《活着》”,而谭sir加的视频标题《感动千万网友最真实的声音“往前看”:“福贵”大爷淡淡地活着,笑着面对惨淡人生》,亦用到了余华小说《活着》的主角的名字“福贵”。
只是,余华小说里的地主后代“福贵”更多是自己“作”的,而这位现实版“福贵”乐观、勤劳、善良,没有怨天尤人,这样的形象是亿万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实在看不出哪里“作”,“命运却依旧如此不公”。
当然,笔者是从来不信“命运”的,如果人民公社还在,现实版的“福贵”想必不用如此辛劳、奔波吧?电影《牛角石》里“反单干”最强烈的就是村里的那些鳏寡孤独,因为新旧社会的两重天让他们有切身体会——集体主义的消亡,只会让他们成为弱势中的弱势。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讲述了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小说描写的真正悲剧在后面,随着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活着》无疑是一部虚无和解构革命历史的文学作品。跟众多伤痕小说一样,它拒绝了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忽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几亿亿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变革,而把目光聚焦于不到人口1%群体的地主后代的命运,即便这1%的命运在伤痕小说里很大程度上也是曲解、虚构——因为毛主席说过,“地主也要吃饭”,现实政策亦是如此,当然在某些基层的确存在过“左”的执行——不过,过“左”的根源正是深刻的阶级仇恨,这又从反面诠释了革命的正义性。

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活着》中葛优饰演的“福贵”
《活着》出版于1993年,是余华文学作品的一个分水岭。跟昨天本号文章提到的贾平凹一样,市场机制的开启,让大多数文人主动选择向“政治和市场投机”。到余华2005年出版的小说《兄弟》,这样的“投机”已经发展到顶峰,以致于他的作品受到那些曾经欺凌过中华民族的八国联军后裔的疯狂吹捧,仿佛他们祖上的侵略就是要传播文明。
而余华本人实际上又是一个复杂体。
与王朔同一时代的余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奠定了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气质;
“艺术家应该深入生活,深入到群众中去,去感受他们的痛苦。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段话出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在余华这一代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不认同毛泽东时代的余华,又不自觉地在践行着毛主席的“指示”。
余华生于1960年,在他形成艺术感觉的时期,正是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天空、“阳光里伸向天空的树梢”、正午、街上的人、才呈现它们各自的本真状态!余华曾经写道:“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我喜欢喝农民那带有苦味的茶水,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话。”这样的经历给了余华这一辈文学作品的“真实感”以及浓烈的平民情结。
然而,余华、王朔们的青年时代又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向私有转换后,“我”的感觉愈加明显,“文学前辈”们从百姓中间重新回到“九天之上”,满腔的委屈写尽的是革命的诽谤;余华们一面彷徨无措,一面却不失青春热血、希望成为时代弄潮儿,走在了诽谤的前列。
“放眼看世界”的80年代,他们惊呼“中国为什么这么穷,老百姓为什么这么苦”,全然忘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史,忽略了别人“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的事实,忽略了老百姓从一穷二白向“已经不那么穷”的变化,无视前三十年的奋斗史,余华作品对前三十年的描绘,就形成了“局部真实”和“整体不真实”共存的怪异状况。
他们用最恶毒的笔调来控诉,以80年代看到的身边的底层见闻去还原前时代,以至于读者惊呼,“他们所写的真是现实啊,有些地方的现实比小说还要黑暗”——显然,这样的控诉对余华来讲不简单是文人的自怜,更有着对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这一点跟方方、贾平凹完全不一样。
80年代的历史剧变造就了控诉对象的错位,这个文人口中的“黄金年代”,其实是市场和私有的开启,这才是底层困境的开始和真正根源。这样的错位在今天同样在发生着……
不过,在笔者看来,余华、王朔等人其实是理性上的精英主义于感性上的平民主义的复合体,或曰“理性上的右派,情感上的左派”。
不必怀疑余华身上的理想主义和平民情结,几年前,余华写过一篇杂文《毛泽东会很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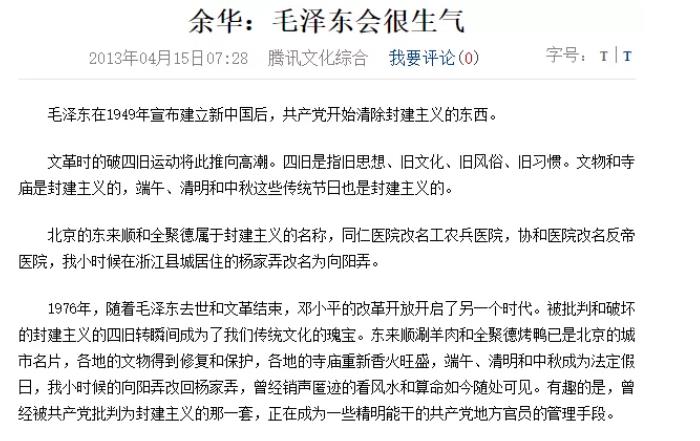
余华、王朔对毛主席,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不过,他们对毛主席在某些方面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过了今天某些自称“怀念毛主席”的自干五。
毛主席说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如果说“马克思”代表的是“平民立场”的话,“秦始皇”显然就代表着一种“宏大叙事”——奉献、牺牲、着眼长远。
余华们在虚无主义的时代背景中迷失了方向,他们一面具有平民情结,一面又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宏大叙事,最终成了“理性上的右派,情感上的左派”;而那些只讲“宏大叙事”,丢失了“平民情结”的人,就只能沦为“理性上的左派,情感上的右派”——当他们看到墨茶、周秀云以及现实版“富贵”,第一反应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
如果毛主席看到余华作品里虚构的《活着》变成了现实,一定也会很生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