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731 到朝鲜战争:
日美的早期对华生物战与战后黑白颠倒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开始精心策划扼杀中国战略。通过制造朝鲜战争控制朝鲜半岛、进而绞杀中国,是其战略蓝图的重要部分。源自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为美军提供了生化细菌战的宝贵资料,它们的用武之地也迅速到来,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投入实战。

早在1950年12月,当美国及其率领的联合国军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提出一个计划:使用生物细菌武器。1951年底,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生物战。1952年1月底开始,美军飞机携带感染了鼠疫、霍乱等十余种细菌与病毒的跳蚤、苍蝇、蚂蚁等昆虫,多批次向朝鲜的志愿军阵地等四十余个郡发动了生物战。不久,霍乱等在朝鲜半岛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许多朝鲜民众、志愿军战士都被感染。除了空投生物武器的途径之外,美军的步兵与陆战队重武器连也都参与了生化战。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秘密被中方捉获的美军飞行员证实,他们承认,自己的飞行任务是生物战。如1952年,被志愿军俘获的二十多名被俘美军飞行员陆续交代了自己实施生物战任务的经过。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秘密暴露后,美国政府立即全面启动了“贼喊捉贼”舆论攻击战。
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出面,将这些飞行任务说成是“普通常规的”;另一方面,一些国会议员与中情局一同高调渲染一个谎言故事,称这些飞行员是被共产党研究出来的先进的洗脑技术“洗脑”,才进行了有关美国生物战的“虚假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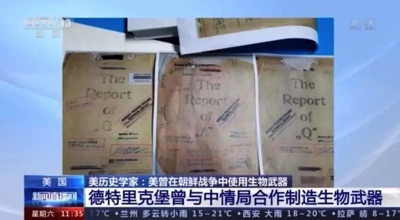
在西方的话语权垄断下,有关共产党对美军飞行员进行“洗脑”的妖魔化宣传,至今甚至已成为被西方公众普遍接受的“历史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情局特工爱德华·亨特(Colonel Edward Hunter )1951年出版的《在红色中国的洗脑》(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一书。1958年,在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听证会上,亨特“作证”称,”洗脑术”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一个巨大威胁,中国人在使用这些“非美国”术,“非美国”意即这种手段是美国绝对不做的。
这场针对中国的黑白颠倒宣传战不仅为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制、脑意识控制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遮掩,并将美国打造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美国社会本来就具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反共与近乎变态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情结。这些有关共产党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也有效地激起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变态恐惧与敌意,并为美国大力开发新一代杀手锏武器提供“自卫”辩护,它向公众提供的惯用“逻辑”就是:共产党国家在使用这些新一代非常规战手段危害美国,所以我们也必须发展这些武器,才能捍卫美国及美国人民。
在西方研究者中,对美国实施生物战的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学家史蒂芬·艾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 )及爱德华·哈格曼(Edward Hagerman)。他们的调查结果于1999年正式出版,《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by Toronto's York University historians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1999,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在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汇集了大量资料,通过一系列对知情者的采访及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得出了一个无容置疑的结论:“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生物武器”。

为了反击这个指控,英美为轴心的西方“自由世界”掌控的媒体、出版业、学术界、科研界等各方被发动起来。1998年11月16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布鲁斯·奥斯特(Bruce B. Auster)的一篇文章,恰好赶在《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正式出版的几个月前,这个时间选择是十分刻意的,是“先发制人”,首先抢夺话语权。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奥斯特忠实地重复着中情局几十年前编织的妖魔化宣传战台词:任何指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说法都是“骗局”。为证明这套台词的“无容置疑”,奥斯特还以所谓的“苏联资料”作“佐证”。
实际上,在苏联崩溃后,在美国无底洞般的大量金钱等贿赂下,众多的俄罗斯精英被收买,情愿为美国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从尖端武器研制,到按照美方需要编织各式各样的故事、伪造各种所谓的“苏联历史资料”。如此,本来属于中情局等美国非常规战机器上编织的妖魔化宣传经过“苏联”这个奇妙的涂料,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苏联秘密档案”,被许多人视为“历史研究”的“更可信”的资料来源。
奥斯特并无查清历史真相的意愿,如他对《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中展示的大量的、无容质疑的证据毫不感兴趣,尽管这本书的两位历史学家作者甚至主动要给他寄去这本书,希望能共同探究历史真相。哈格曼如此讲述了奥斯特对这个建议的反映:
“我主动提出要把这书寄给他。他说,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会让我的出版商知道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要这本书。”
奥斯特究竟是否受雇于中情局的抢手?他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消除质疑者们的疑虑。当然,奥斯特本人,就如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构》的作者——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样,对这样的话题十分反感并矢口否认。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据说,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但《美国和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长期却未能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对比一下另一本书在中国的命运:本来是为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提供合理合法的“道德”辩护、通过妖魔化慈禧太后“奸诈、淫荡”来丑化整个中华民族的宣传战一部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这是他的官方档案身份)埃蒙德·巴恪思手执一封来历非凡的推荐信从英国抵达中国,并在后来开始出手所谓的清朝宫廷“回忆录”,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权威”信息来源。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大作就在英国本土被暴露是纯属其本人“淋漓尽致地发挥淫荡的想象力”,通过“纯属小说的虚构与信手编织”而打造出的妖魔化宣传式写作。不可思议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巴恪思“日记”不仅被许多人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史料,巴恪思甚至被升格为“慈禧太后包养的洋情人”,《太后与我》不仅被出版,还在学术界与出版界引发轰动效应,甚至被高调宣传成“尘封68年之后才首见天日”的“清宫秘史”。)

当中国对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显然不感兴趣时,对中国进行五花八门妖魔化的舆论战大军却踏遍世界,横冲直撞,把“贼喊捉贼”的丑戏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一直刻意隐瞒的,不仅包括朝鲜战争中美军自己的生物战罪行,也包括二战中日军生化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生物战及活体人体试验。为此,美国继承了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惯于使用、已炉火纯青的一门“国技”,就是人前、台后两张脸皮的娴熟调换。一个典型范例,就是围绕着《战争披露法案》的“演出”。
九十年代,公众的一个呼声越来越高——要求美国政府公开一直被保持缄默的相关秘密档案:在二战结束之际以及二战后,美国如何掩护纳粹德国精英逃亡、并让他们为美国继续服务的。在这些呼声的压力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通过《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案》,并于1998年被克林顿总统签署为正式法律。
在这个时期,一系列事件也把长期被美-日精英力量联合压制的日本战争罪引入公众的视野,包括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生物武器试验、生物战、南京大屠杀等罪行,如谢尔顿·哈里斯(Sheldon Harris)的《死亡工厂:日本的生物战1932-1945及美国的掩盖真相》(Factories of Death:Ja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张纯如(Iris Chang)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等研究者的作品、一系列被日美法律界精英们联手推翻的对日诉讼案等等。当时,许多人呼吁《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案》也应适用于日本,继而引发一些公众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日本战争罪相关秘密档案的运动。
但美国政府再次采取了拖拉迂回战术,直到2000年12月,才在压力下正式确认把日本包括在《战争罪行披露法案》,并通过了《日本帝国政府披露法案》(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Disclosure Act)。但这些所谓的“披露”不过是面对公众的又一场公关戏。扫描一下那些被“披露”的档案,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秘密档案或是仍被隐藏、或被涂抹删除得面目皆非,根本无法进行有意义的阅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将“调查”的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从拖拉变为“主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开始主导对日本战犯的行为展开 “调查”。
二战后的东京战犯审判中,那些潜在的证人、潜在的可为公众提供真相信息者被谋杀、威胁、灭口。在半个多世纪后,这个模式仍同样适用。

虽然官方对年轻的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的死匆忙定性为“自杀”,这个定论一直被质疑。也一直有一种说法,在分析了张纯如“自杀”前的一系列事件后,判断这是典型的脑控“被自杀”,是对张纯如这样拥有独立调查倾向的历史研究者进行“中和”。这种说法是否纯属空穴来风,这值得每一个关注现代一体化战争(尤其是种种烟幕掩盖下的脑控技术发展)的有心人去深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彻底“中和”是一个典型手段,另一个常用手段,是把那些勇于面对自己的战争罪、积极提供证言者列入“黑名单”,进行不露声色的惩罚打击与边缘化,日本的篠冢良雄、东史郎曾被拒绝入境美国一事就是这个手段的范例。
篠冢良雄曾服役于731细菌部队,参与了在中国的人体试验。1973年,他出庭作证表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东史郎曾参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98年,两人计划以《二战时被忘却的亚洲大屠杀》为题发表演讲,并因此访问美国。篠冢良雄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
谁在害怕他们为公众提供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生物战、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真相?在这个把“信赖上帝”的口号印上纸钞、铺天盖地炫耀的国度,良知,显然是个稀缺商品。
在“自由”西方世界,含而不露地垄断舆论及信息流通、隐而不显地控制媒体话语权、对信息“自由”进行覆盖一切的无形“审查”,这一切都是“自由西方”主宰现代国际秩序的一把金钥匙,一门冶炼得炉火纯青的帝国权术。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惯于把援引海外报道甚至美西方的官方言论(通常是黑白颠倒宣传战)当作自己的新闻来源,有意无意中成了美西方的宣传喉舌。在对美国拒绝篠冢良雄等人入境的报道中,中国多家媒体以“美禁止35名日战犯入境”之类的题目进行报道,“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之类的表述成了这些一些媒体为中国公众提供了解国际新闻“真相”的信息来源。根据这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逻辑,美国反倒成了“主持公正、嫉恶如仇” 的正义化身。

作为世界“经济第二”的大国,长期缺乏自己的话语权,任他人操纵自己的大脑意识,在一体化战争的时代,这就如同战士不带枪、甚至喝着敌方的迷魂汤上战场。
虽然美国长期否认自己的生物武器的研发与日本731部队之间的纽带,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起至今,一些正直而有勇气的西方学者一直在挖掘真相。如五十年代早期,《中国月刊》(China Monthly Review) 杂志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John William Powell),就在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针对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六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
1980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鲍威尔发现了一份备忘录,该份备忘录卷入麦克阿瑟将军、查尔斯·威勒比将军及其他相关人员,揭示了美国与日军生物武器研制之间的秘密关联。针对该备忘录,鲍威尔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发表在《关心亚洲学者公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及《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但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保持着默契的集体缄默,话语权及全球信息流通的垄断导致世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仍一无所知。
在日本群体内,也有一些正直的研究者发出良知的声音。如旅美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在进行大量调查后,出版了《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记载了自己如何发现了石井四郎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秘密协议。青木富贵子叙述到,自己是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看到了令她震惊的《镰仓协议》,其中包括“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受战争罪责追究” 等内容。

从许多方面看,被美国牢牢主宰的东京审判堪称司法史上的一个浓重污点。对生物武器研制的严加保密是其中一个要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要确保二战后对日本的全方位、不可撼动的控制而达成的一系列幕后交易。对日本一些真正战犯“清洗”的同时,将一些替罪羊或不方便的拦路石及时清除,是这个进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幕后秘密交易是美国二战后全球征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在亚洲付诸行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那些积极参与战争掠夺、屠杀、奴役中国等亚洲人口的日本精英从战争罪中解脱出来。
最初参与策划这个谋略的核心人物包括胡佛、麦克阿瑟、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h Grew)、菲勒斯准将(Bonner Fellers)等人。菲勒斯是美军战略情报局官员、美军心理战负责人、麦克阿瑟的心腹亲信,其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美国占领军与日本皇室之间的协同。他曾写了数个极有影响力的备忘录,说明为什么要保留日本天皇、为什么清洗天皇家族的战争罪责有益于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控制、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在代号“黑名单行动” (“Operation Blacklist”)的秘密行动下,菲勒斯等人负责与东京战犯审判中的被告人见面,让他们彼此协调证词,以便让天皇及其家人免除战争罪的起诉。
为了控制东京审判中的证人、确保东京审判“走正路”,一个特别秘密基金也被建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秘密基金是以东京战犯审判中担任检察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名字来命名,叫“季南基金”(Keenan Fund),并被研究者指控用于贿赂、恐吓、谋杀证人、伪造证词、寻找替罪羊、掩盖战争罪行的证据等活动,包括隐瞒731生物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各种活体试验的战争罪行证据、向美军生化武器研制基地德特里克堡秘密转移资料等行动。不仅如此,“季南基金”的一大部分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入日本的地下黑帮网、极端右翼组织、宗教团体等美国代理利益网络,成为二战后美国全面控制日本社会的秘密武器。
“季南基金”不过是冰山一角。战后在日本也涌现了大一批秘密基金,除了“季南基金”,“吉田基金”(Yoshida Fund)、(Keenan Fund)、M基金、“黑鹰信托基金”(Black Eagle Trust)等等,都是典型例子。用于建立这些基金的财富来自当年日军从中国等亚洲国家掠夺的天文数字般价值的庞大财富。

这些秘密基金不仅被用于贿赂、暗杀等“特别行动”,也被广泛用于建立五花八门的门面公司和组织,被用来收购、兼并,用以渗透、控制各种电视、广播、杂志、报刊、出版社、娱乐等媒体网络,以及教育和科研机构、甚至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一切都在确保美国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掌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此,日本执政党及其各种化身转型的党派、所谓的“在野党”等政治精英权贵家族、军界、法律界、媒体、学术教育、宗教组织、娱乐界、体育界、工商金融界、秘密警察、极端右翼势力、地下黑帮网络等等,无一不在这个覆盖日本社会的蜘蛛网控制之内,巩固这些势力与美国各界同行之间的一体化融合,通过这一体化网络中的精英群体“以日制日”,美国也从幕后有效控制着整个日本社会,并进而“以亚制亚”,把日本打造成了一个对整个亚洲进行“分而治之”、反华制华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将731部队及其与美国生物武器研制之间的纽带等资料及研究状态保持绝密状态,也让美国确保维持新一代战争杀手锏的优势。
如今,许多国人有个误区,误以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是在“卧薪尝胆”、借同中国开战增强自己的军力以最终向美国复仇。这种想法不仅对日本的国民性本质缺乏深度理解,也对二战后至今美国对日本社会隐而不显却滴水不漏地进行全面窒息性的主宰与奴化改造这个无形现实缺乏全面了解。
自二战结束至今,为日本天皇及日本国家形象整体“清洁”、“上光”、“镀金”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并得以成功地顺利实施,日本对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的掠夺与经济侵吞的证据与资料也都被“自由民主世界”诸国压制、清除——从其档案中、数据库中、历史教育中,许多资料至今仍被归类为“机密”向公众隐瞒,大量水军也在网络上散布种种黑白颠倒的舆论造势,在中国的一些网络,甚至把天皇家族亲自督导的“金百合”绝密行动说成是“不存在”,这一点与“南京屠杀不存在”造势同出一辙。

为日本与德国的“镀金”工程究竟有多成功?一件小事足以说明问题。
2013年5月,以英美加等盎格鲁-撒克逊势力为核心的咨询与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 (GlobeScan)与PIPA进行的每年一度国家形象评级中,“全球公众”认定在国际上扮演了最积极角色的国家是:德国、日本。
这个全球“民意调查”结果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多年中,在该类“民意调查” 项下,偏偏是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领域做出了特殊贡献的纳粹与法西斯战争机器,在世界“最受欢迎国家”评比的全球“民意调查”中,一直高居榜首,玄机何在?至少可以说的是,二战后,在美西方协调一致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战造势下,这二者都被套上一个耀眼的“和平”光环,并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对华终极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的大规模开发生物武器方面,美国起步于四十年代,并借助于德国纳粹与日本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人员迅速领跑世界,实际上,长期以来,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精英们对削减特定种族人口这个主意痴迷到癫狂程度,并在刻意针对种族的生物武器及人体试验领域的研究拥有漫长的历史,不仅十八、十九世纪就在“新大陆”有意使用天花消灭印第安人、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消灭土著人口,而且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财富家族就被作为代理门面,活跃在军-政-情-工商-金融-科技-文化等一体化无形战前线,在“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交流”等招牌掩护下,大力推动新一代种族灭绝战。
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长期保持集体缄默的另一个“家丑”是,不仅希特勒的纳粹党制定的种族优生法律的样板来源于美国,不仅日本的生物武器开发的最初灵感与技术源头也可追溯到美国,而且这一切都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纽带。

今天,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中心与实验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一些与纳粹德国与日本生物战有着千丝万缕的纽带,著名的包括普拉姆岛、德特里克堡这两大非常规武器研制中心,分别与纳粹德国、日军的生化武器研制项目密切相关。而今,历经近八十年的发展,控制管理着美国数千个生化实验室的,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联手军方及情报机构。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于1946年组建时,本来就与军事项目密切相关,它的前身是战区疟疾控制项目,最初被称为“防治传播疾病中心”。这个名义上为“捍卫美国公民健康”的公共卫生组织,长期以来就不断被指责是由“白人至上主义”情结的纳粹势力及军方控制,与美军、世卫组织一直密切合作,基本上是一明一暗、合演双簧戏的家族兄弟。实际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并非唯一受到这种指责的美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受到类似指责的美国政府机构及国际组织一个接一个。
在这个一体化战争的时代,十分值得考究的是,美国农业部、能源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它们都名符其实吗?
二战后,世界早已大踏步地迈入了一体化非常规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思维不能依旧停留在二战时期,按照“和平”时期构建国家的安全与政府管理体制,甚至把西方的行为误读成“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思维”。
不是西方“仍在使用冷战思维”,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仍停留在原始的常规战时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