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当代《金瓶梅》”
穆 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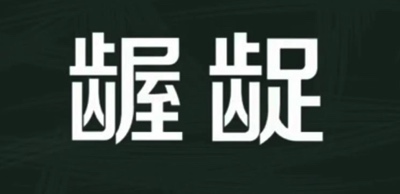
一个时期以来,“当代《金瓶梅》”一词,在文学界颇为流行且热火,仿佛令人觉得,一部“当代《金瓶梅》”的出现,是非常“伟大”与“荣光”的事情,值得大加颂扬与褒奖,以广其闻。而文学界则更是兴奋异常,视“当代《金瓶梅》”的诞生为胜事,以为能写出“当代《金瓶梅》”者,非大师莫属。当然也有的同行作家不以为然,只是惮于文坛主流的认可、推崇,只好把“百家争鸣”抛诸脑后,缄默无语。
不过这种文学景象,注定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果然,近期随着社会群众对“屎尿诗”的群起批评,“当代《金瓶梅》”的作者也同时出现在了舆论的前台。“屎尿诗”以恶浊的气味污染人文环境,“当代《金瓶梅》”则以色情坏人心术,两者前后映照,互为表里,倒也少见!难怪民众的一片汹汹质疑之声,竟然成为建国以来文坛仅有之景观!
所谓“当代《金瓶梅》”,是一个褒奖词。最早所指是《废都》,近期所指是《暂坐》。这个说法,究竟出自谁人之口,不得而知,但从近来《暂坐》荣获大奖来看,证明对“当代《金瓶梅》”的认定,是不会虚妄的了!
然而,我对此却是颇为怀疑的。我不怀疑今天的作家能不能写出明代《金瓶梅》那样的文字水平,我怀疑的是,今天的作家,文学创作以《金瓶梅》作为崇拜、模仿的对象,并受到学者专家的高度赞许、推崇,这到底是对《金瓶梅》情有独钟还是别有衷曲?中外古今,文学经典不少,为何独一看好《金瓶梅》?模仿经典也好,蹈袭故旧也罢,这同“伟大”与“创新”毕竟是毫不沾边儿的。何况,《金瓶梅》这种以色情描写著称而备受历代争议的作品,有什么必要拿到今天来张扬崇拜呢?
《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明代著名文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作家冯梦龙从他人处见到一部手抄《金瓶梅》,十分惊喜,便怂恿朋友拿钱刻板印刷,结果无人敢出面做这件事情,原因是担心“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将来阴间的阎罗王会追查责任的!①由此看来,《金瓶梅》从写出之后就是一部只在少数人手中偷阅的禁书。为什么要禁?原因很简单,就是它能“坏人心术”!
《金瓶梅》是一部“秽书”,这是无可置疑的。鲁迅认为,“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②这里包含有两个意思:一,《金瓶梅》写作的时代,是一个“万事不纲”的“衰世”;二,《金瓶梅》所以是一部“淫书”,是由于当时那腐朽的社会风气促成的,当时那种普遍的“腐朽”,已经成了“时尚”,《金瓶梅》中的那些荒淫的描写,就是这种“时尚”的反映。
《金瓶梅》所以能够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是因为它真实地描写了明代社会士大夫阶层腐败的丑恶现象,赤裸裸地表现了那时的社会病态,是可以作为一部“世纪末”荒唐堕落的心灵史来看的。这就是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此我们便明白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是泛滥的淫欲描写;《金瓶梅》思想特色,是一首衰世的悼亡曲。这些,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功力,确都是独一无二的。
文学是表达思想的艺术。思想不同,书写表达也就不同。文化的颓废,往往首先是思想的颓废。文学的颓靡之作,与思想的颓废密切关联。有的人把过分的色情与淫欲描写,说成是塑造“人性”的需要,其实并不尽然。不错,文艺写“人性”,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人性”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并非仅是“男女之性”。杀身成仁是“人性”,报国牺牲是“人性”,洁身自律是“人性”,胸怀道义,嫉恶如仇也是“人性”。而我们有的作家,为什么总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津津乐道呢?崇拜《金瓶梅》,仿效之,追模之,以此浪博名著遗韵,被评家捧举为高端,以之为荣。这种心态与操弄,如果不是别有用意,便是纯属误识与误导!
今天颂扬《金瓶梅》,既不合时宜,也无艺术新意,有之,大概只是生理欲念的抒泄吧。而男女性爱的露骨描写,有伤风化,害大于益,视为“败俗之音”,似不为过。醉心于以颓靡为乐、以疮痂为美的“审美”艺术,究竟价值几何?每读李煜那“亡国之音”的诗词,想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话,对于“雅正”与“狭邪”的鉴别铨衡,难道不应当引起重视吗?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家的感情与创作思维,是离不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无论是现实题材抑或历史题材,无不如此。今天仿写《金瓶梅》,与时代精神相悖,与社会环境不合,这样的书写,极不可取!《金瓶梅》作者是假借《水浒传》中的北宋人物,而反映作者所处的明朝社会的。据专家考证,作品的时代大约在明朝嘉靖或万历年间。而此时的明朝,“是社会风气最黑暗、最污浊、最腐朽的时代。”③明朝末年,社会腐败,阶级矛盾加剧,贵族士大夫酒天花地,荒淫无耻,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在满族入侵与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寿终正寝。当时《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低级趣味的精神需求,在《金瓶梅》中极尽色情描写,以取悦读者。这是《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应该说,在《金瓶梅词话》以前或同时的我国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④很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与《金瓶梅》的时代,大不相同。一部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模仿学习,思想倾向则不能与时代精神相悖。否则,其文学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其现实意义也值得怀疑。因此,出现一部所谓“当代《金瓶梅》”,作为百花中的一“花”,以“创作自由”的角度目之,可以有存在的理由,但决没有被吹捧而成为“花中之王”的理由!如果硬要将它当做“化腐朽为神奇”之作,那么作为作者,那是一种心理癖病;作为捧者,则是在欺蒙作者和读者。欺蒙作者事小,欺蒙读者事大。作者、读者、评论者,如此三者的诡异气氛,怎不令人忧虑深深!
因此,我倒是希望《废都》与《暂坐》,远离《金瓶梅》为好。或者只是袭其皮毛,未得真髓。这样,问题倒还小一些。否则,如果真像被人称誉的那样,《废都》、《暂坐》,从里到外,就是恰恰的“当代《金瓶梅》”,那就麻烦了!为什么?明朝末年腐朽的土壤,产生出了文学奇葩《金瓶梅》;面对“当代《金瓶梅》”,读者必然要问:“当代《金瓶梅》”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三思之后,人们将怫然惊呼:“今天也与明朝末年那样腐朽了吗?”岂不知,“当代《金瓶梅》”的出现,文学界把它当做一个“大作家”搞出来的“大成果”,对于国家来说,却不啻遭受了一次侮辱——对时代的侮辱!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吹捧《暂坐》为“当代《金瓶梅》”的先生们,你们相信今天的中国有着明朝末年那种腐朽衰亡的征象吗?你们相信《金瓶梅》重现于今日的合理性吗?
奉劝褒奖“当代《金瓶梅》”的文学“权威”们,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弘扬文学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多做点事情吧!否则,任何为利欲而苟容的作为,任何拿公器以徇私的勾当,皆非君子之行,而是对文学这个圣洁殿堂的严重玷污!
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五百年前《金瓶梅》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以雄健的脚步、伟大的理想,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在消除腐败,净化生态环境,加速繁荣富强的奋斗中迅速崛起,这是世界所公认的。《金瓶梅》的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金瓶梅》一书,只能作为艺术遗产存在于文学史中,要它在今天“返魂重生”并为其推波助澜,恐怕人们是要质问的:自古文章重风骨,甘心颓靡,意欲何为?
今是昨非不同代,劝君莫颂《金瓶梅》!
注:
①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1933年《文学》杂志第一卷,转引自《金瓶梅论集》,1986年版,第1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
③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④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作者系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