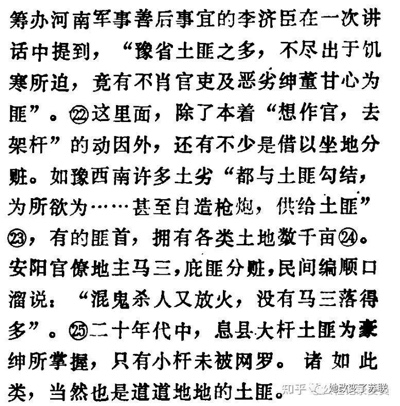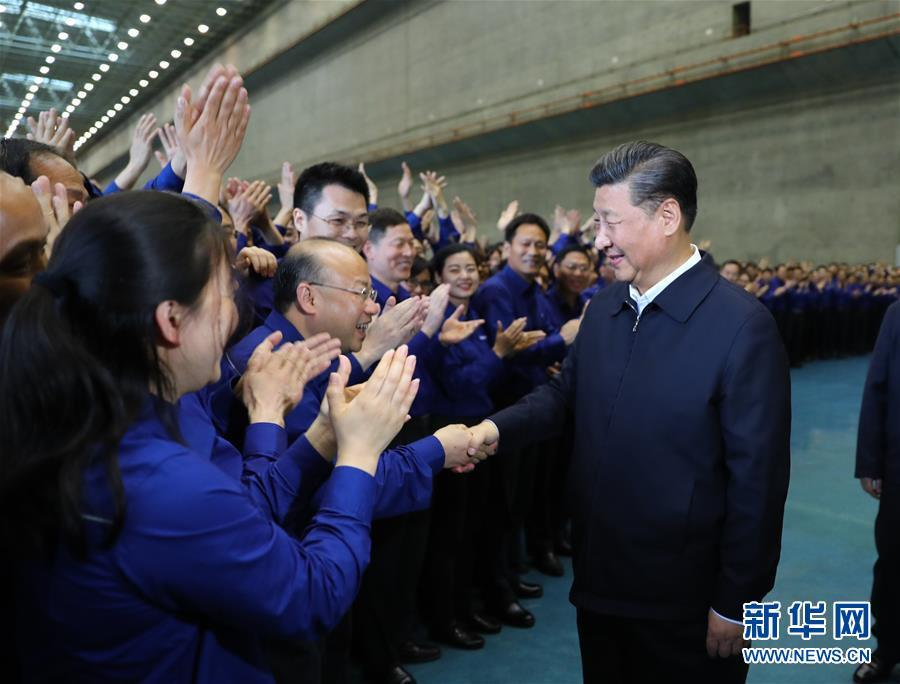地主阶级的罪恶,仅仅是“半夜学鸡叫”吗?
许多关于论述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地主阶级的文章,给地主洗地的自然是只配得到我憎恶的唾骂,而许多批判基调的文章也未能写明中国地主阶级真正的丑恶——以及这种丑恶有多么令人发指,这里容我稍作补充一二。
“在绿林朋友间是那么吃香,别说他的话人们宾服,就连他的唾沫掉地上也会叮当响。七少的声望一天天地大起来,方圆十几里内的老百姓没人不巴结,连搬住在城里的地主们也只好买账。如今七少俨然是地方领袖,尤其是茨园寨地主集团的一座靠山”
——姚雪垠《长夜》
1、绅匪勾结
从晚清到民国,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的局面,许多地方上的富户豪绅办团练(晚清)、编民团(民国)。
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防匪”“抗匪”很容易转变为“联匪”“济匪”。
如同当时兵匪角色经常互换一样,“绅”与“匪”的身份也不时转换的。
曾国藩就是靠办团练民团发家
如豫西南匪患的猖獗离不开地主豪绅的支持。
大地主为自保计,往往暗中支持匪首,窝藏匪众,而土匪为生存安全计,也愿意与其发生联系。
豫西南地区匪股横行,与富户豪绅暗中资助、勾结有关,后者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可以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匪股帮助。在匪股方面来说,完全是为了生存、发展,至少可以随时窝赃、逃避追捕。
1923年,筹办河南军事善后事宜的李济臣在讲话中提到:
在鄂豫边界打游击的周骏鸣曾做过“匪运”工作,他了解豪绅与土匪间的关系,并表示:
“到处闹土匪,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种地也不能安生,很多地方打起了土围子,以后发展成建碉堡。土豪劣绅利用打围子修寨墙进行勒索,派款买枪,他当寨主。很多寨主还通土匪,把枪交给人家,这叫放外队,他坐地分赃。”
1937年,他在给中共的报告里说,在桐柏山地区“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
1929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童长荣在谈到河南的军阀、豪绅、土匪之间互相勾结时也说道:
“土匪是军阀战争的傍生物,同时又是军阀地主豪绅、富农剥削制度的另一方式,因为只有他们有枪可以做土匪的领袖。政府方面曾派人在南阳县展开调查,当地阶级分化、土地集中的现象比较显著,甚至有好几家拥有5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该县匪股颇多,但没有一股攻击过这些大地主的寨子。”
2、借匪敛财
土匪滋盛的豫西临汝、伊阳、宜阳一带,土匪盘踞之地,人民外逃,田地荒芜,荒地日久往往落入少数豪绅手中,学者们认为“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
同时,土匪活动也使富户不敢再购置土地扩大产业;绑票勒索,又使很多人为回赎不得不卖掉地产,土地价格呈下降趋势。
调查显示,民十七年到民二十二年,被调查的地方“汲县第一区的地价,五年中就跌落了1/6;修武六区、新乡四区、滑县九区,跌落得更多,几在50%左右。”
当时的资料显示:
“豫南地价跌落更比北部及西南部显著。信阳近城五年前每斗(注:“斗”信阳土地单位,究竟多大说法不一,约略一亩。)五十元的地,近年来三十五元无人过问。”
那些掌握民团武装的武人和地主,有武力保卫财产、有财力购买土地,于是农民的土地迅速向他们手中集中。
在豫西和豫南,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贫困程度较深,生活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豫西、洛宁、新安、渑池等县,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比比皆是。
河南地主修建的村寨,甚至有城墙和护城河
洛宁河底张家占有土地500余顷,形成富愈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 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 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这也是产生土匪的主要原因”。
据1933年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的调查,河南西部和南部大地主较多,北部次之,中部最少。 南阳内乡罗姓家族的几个地主,竟然拥有良田六万亩;信阳罗山的刘楷堂原有稻田几万亩,后来虽然因为分家和出让的原因,田地逐年减少,但其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二千亩以上。
豫南其他各县田权集中的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显著。 因此:“豫南各县农村中近年来的‘动乱’,在这里不难找到客观的根源”。
正如鄂豫边特委分析当时形势指出的
“在农村土地关系发生迅速的转变”,“土地转移到少数封建大地主手中”,豪绅地主形成。这些豪绅地主“为要维持着封建统治,更尽量的扩充民团武装,每个佃户派枪一支。……这些少数大地主更把持了全县的政权,形成了割据政权的形式。”
甚至1932年,河南省主席刘峙在豫南围剿红军前发表演讲也表示,“豫南农村多筑寨自守,各寨寨主概系,田连阡陌,” “平日把持一切,鱼肉乡民”。
可见:中国地主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丧心病狂了,连先总统 蒋公的爱将“猪头”刘峙都看不下去了。
3、匪绅政权
王怡柯在论及农村豪绅自卫之流弊时有过如下叙述:
这一点都不夸张
如唐河县,豪绅操控地方政治的特点尤为突出。据中共方面报告:
“唐河县政治自前清到现在,完全操在割据地主的总代表曲凌霄一人手中……唐河县因为有这样豪绅统一的势力,故在以前无论国民党改组派等等,统统不能打入下层群众中。”
在泌阳县,豪绅王友梅、王友堂、范焕台等左右地方政局。
据早年在鄂豫边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张旺午回忆:
“无论谁来他们都欢迎,谁来都给谁合得来……泌阳的形势翻来复(覆)去就是几个绅士当家。那时的县长都是由军队委派的,他来他走,军队变,县长变,绅士们不变。”
这下流水的军阀,铁打的豪绅了。
国民政府的调查报告称:
“区长们凭借他们的资格和地位,在乡村中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势力。他们包揽词讼,他们任意派款,甚至残杀善良,以造成个人的专横,扩大个人的权力。”
在南阳、唐河一带,据国民政府调查:
“区长初为在省城受过训练的青年,因应付不了复杂的环境而渐渐的受淘汰。乡长初为声望素著的世家长老,或由小学教员而变成的乡村绅士充之。久之,因苛捐杂派的烦难,除一部分变做土劣外,余尽转入地痞流氓之手。这种现象,唐河较南阳境内尤甚。”
中共地下联络员王锡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指出:
“(南召)基层政权一向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担任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大都是地主豪绅或其代理人。地主越大,当的官也越大。枪支武装也都在他们手中掌握着。深山区的一些联保主任、保甲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实际上是‘山大王’。”
中共豫南巡视员郭树勋也向中央报告:
在豫南地区,“乡村及偏僻县份的统治权,仍然操之于豪绅之手”,“许多城市(如泌阳、桐柏等)由豪绅所领导的民团统治着,因此豫南完全为军阀军队、土匪、豪绅的民团杂色队伍的分割统治。”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豫西南时,发现这里不宜建立根据地。程子华、刘华清晚年回忆:
“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统治严密,地主全都修了围寨,把群众圈禁在里面,使我们无法接近,不能开展工作。”
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最终决定离开豫西到陕南开辟根据地。
一支民团队伍,可见ZB-26轻机枪
在方城县:
土豪劣绅利用手握军政特权巧取豪夺,大量吞并土地。大士绅白太庚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占有县城附近良田3600多亩,瓦房数百间,有钱有势,曾经是当地“脚踩着衙门堂乱动弹的人家”。
方城县的民团编练、粮食摊派、地方合作事业,他无不参与。方城石头寨大地主周炳轩一出门,二三十个腰插手枪的打手前后护卫,寨内常驻团队,最少时也有100多人。
周家奸污民女不计其数。不少佃户的闺女不等长大就被糟蹋,新媳妇不出3天就得上周家做活,好让瞧瞧丑俊。他们有时持枪强奸,有时威逼进府奸污。
石寨的门楼上,是周家私设的刑场———吊人楼,里面放有踩杠、老虎凳、皮鞭等各种刑具。
在南召县:
基层社会资源控制在掌握地方武装的豪绅(地主)之手。担任民团团长的南召豪绅彭东川外出,总是前簇后拥地跟随者20多个打手。大地主彭五卿,人称“野兽”,奸污妇女50多人⑨。
据中共方面的调查:
“在南召,封建势力是占着特殊地位的,境内几乎全是山,耕地非常少,而这仅有的一些耕地,还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地主手里,大部的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和雇工。地主们都直接拥有雄厚的武力,差不多每一个地主都要有二三十支枪,许多下级官吏如联保主任保甲长之类,都是地主担任的。他们可以任意向民众派款派壮丁,甚至还可以任意残杀民众!”
在唐河县:
大地主李子炎有武装家丁70名,武器600余件:计有小排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长枪300多支、掷弹筒3个,还有很多手榴弹。
从寨门口到外院、内院,日夜站着三道岗。李子炎一出门,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马,跟七八个打手。
如果你是一个当时的普通农民,又能否脱离豪绅的鱼肉呢?
事实上很难,难于上青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社会秩序崩溃,面临土匪蜂起的局势,乡间地主修筑寨墙,组织武装防匪自卫。普通乡民无以自保,被迫依附于居乡地主或村寨首领。
各村寨形成了以大豪绅(地主)为寨首,各佃户、(半)自耕农为寨丁的村寨自卫组织。在村寨内部,佃农及(半)自耕农平时耕种、训练,匪患来临时在寨首领导下充当寨丁,保卫村寨安全。
还记不记得上文所说,“绅匪勾结”呢?
就这样,在一个全面崩溃的社会环境里,在南京反革命军事集团注定无法深入的基层社会中,中国的地主与土匪以一种丧心病狂的智慧,精妙的构建出了一种扭曲的共治联统格局。
直至红旗下的工农大军一扫宇内混沌前,他们仍维系着腐朽的传统中国最后的骨架,亦或者是糟粕。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ls/2023-02-01/79978.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