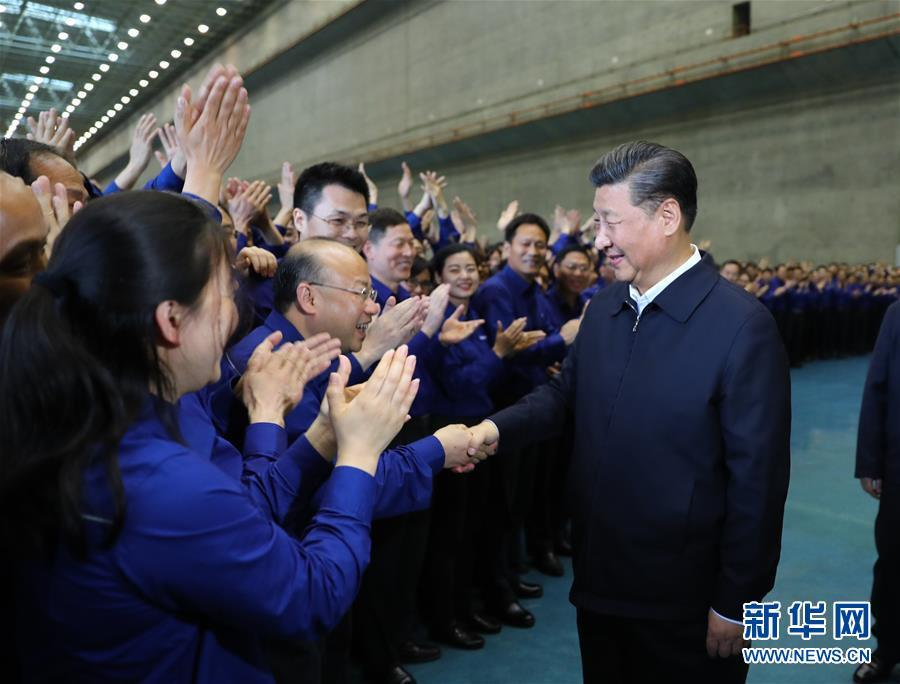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进行初步勾勒与比较分析。
一、引言
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 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民国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2000:456)。80多年后的当下,当美国2001年对内遭遇IT泡沫崩溃、对外遭遇“9•11”恐怖袭击无暇东顾而中国获得举世瞩目的高增长并重新成为世界焦点之际(这与民国乡村建设时西方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并且演化为世界战争可以相比),当代乡村建设也于同期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
作为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的一线实践者,我们不满足于常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类分析框架,认为应该“跳出乡建看乡建”,打破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时空和叙述上的割裂,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通过回到历史脉络,我们尝试指出: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除了百年耻辱和百年抗争外,同时伴随着百年破坏与百年建设,它们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构成了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张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涉及的三个“百年”(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划分,而是宏观意义上对西潮冲击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泛指,重点在于通过指出“激进、乡村破坏、乡村建设”之长期性与平行性,以建立三者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联,强调不同阶段之乡村建设虽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都可视为整体性状态或趋势的一定体现。
二、他毁与自毁:乡建视野下的百年激进
面对外界的批评与不理解,梁漱溟指出自己之所以选择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毁”和“他毁”这两种力量的叠加与互动:“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梁漱溟,2005:197-201)。具体到影响及效果上,他甚至认为“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2005:151、152)。对此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黄宗智也有着相似的认识(黄宗智,2000:21)。
梁漱溟所谈到的“自毁”和“他毁”,一定程度上联系着乡村建设视野下的“激进”反思。在这种视野下,中国近代历史脉络中的“百年激进”既非一般的“冲击-反应”,也非个别人物或派别的思想主张,而是因西方挑战和影响而引发出社会内外各种力量的连锁反应,以及共同产生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势能。“激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刻且全面,但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产业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为更好地切入讨论,下面先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激进”的讨论进行简单回顾。
(一)“激进”讨论简要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80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把握,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正是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思路(杨念群,2001:68)。
在余英时1994年的分析中,激进不是指具体的思想或特定的学派,而是指一种态度或倾向,并在这个层面上将保守理解成激进的对立项。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分析,他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余英时,2006:422)。对于这种激进化进程的影响,萧功秦认为其“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具有与现实国情、政情脱节的倾向”(萧功秦,1999,序言,2-3、314)。林毓生则以“中式乌托邦主义”来指称这种“五四”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它的突出特点是“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同时带有封闭性和排斥性,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几乎没有警觉,反认为这种“中式乌托邦”是一个最能系统地、全盘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运动(林毓生,2006:467-469)。我们认同这种对“破坏性”的自觉,但认为它不是中国“五四”以来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印记,其排斥性与破坏效果同样存在于延续至今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面对各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萧功秦,1999:序言,4)或以之为二元对立框架的讨论,姜义华和陈炎(2000:36)认为:激进主义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应主张跳出“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的立场,才可能避免简单化处理可能带来的新遮蔽。类似的反思在不同论述中也有所推进,许纪霖(2000:41)就认为“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的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杨念群则指出:在这场争论中强调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和强调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者都共享同样的前提——“都是对使用现代化标准衡量近代思想的无条件认同”。但实际上,“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的一种阐说。这实际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杨念群,2001:71-72)。之所以如此,除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与底层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杨念群,2001:72-74)。
这种“激进化”进程本身就存在着内部张力,而非连续单线的过程。有学者就认为从二三十年代起,那些要求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实际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许纪霖,2000:39)。我们认为,这些屏障同样有助于理解本文所述三个“百年”之同时存在与互动张力。
基于以上简要回顾,我们认为现有“激进”论述主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展开,较少涉及经济、生态等领域;过多强调各种层面的“激进”作为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特殊性,相对忽视“激进”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第三世界、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的普遍性;①主要基于知识领袖和政治人物等上层精英的言论和主张,较少从普通民众及具体社会状况(特别是乡村、农业、底层)出发进行讨论,且对各种“激进”间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张力缺乏处理。
(二)双重破坏中的“去脉络”进程
如果回到前文梁漱溟所指出的“他毁”和“自毁”,“自毁”是由“他毁”引发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体现,同时还与“他毁”结合且相互引发,进一步催生出更为激进的社会土壤,叠加构成更为深刻的危机与双重破坏。
比起“他毁”,“自毁”更具广泛性、长期性和隐蔽性。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后者则深入到内地与广大乡村;如果说前者因为战争、侵略、屈辱和不义而面对着各种形式的抵制与警醒,后者则因各种“自强”论述所内含的道德制高点而难以自觉;如果说前者是被动的“遭遇”,后者可以说是某种主动的“配合”。这么说,重点不在于两害相权,而是希望指出其中的双重性与复杂性。
无论“自毁”还是“他毁”,“毁”了什么?这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破坏与信心层面上的丧失,更包括由此所开启的“去脉络化”进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所改变和偏离的脉络,不仅涉及国情与资源条件制约下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基础,也包括国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我们将在下节以乡村为例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下面先从纵向角度简单勾勒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体现与影响。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西碰撞所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对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体系建立有着奠基性意义。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中)体(西)用说”②及其指导下的洋务实践的破产,工具层面之“西化”的有效性受到根本质疑,由此产生着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这些变革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具有“都市本位、工业优先、成本代价向乡土转嫁”的共同特点。“后自强时代”更深刻和广泛的实践对乡土社会与底层民众来说,却可能产生“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这一不期然的效果。
作为“自毁”突显的关键时期,甲午之变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然而1894年只是连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结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挫败,时人面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奋起求变,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逐步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与自救而产生了启蒙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时代主题,以致“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及古老历史在新世纪骤然断裂”(许纪霖、陈达凯,1995:2-3)。由此激发起对数千年农业文明形态与乡土社会(也包括相应的心理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拒绝与批判,进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以农立国-以工立国”论战,外加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以致除经济基础的激进化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产生革命土壤外,对乡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也逐步开始激进化。
从“三农”和宏观视角看,这种对现代化的激进追求并未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中止,冷战格局和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继续为不同形式之激进化提供着强劲动力,并确保了政治正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过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获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与小农村社经济这一基本现实,但迫于外部国际形势与客观环境变化③,为配合当时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更加重要的脉络(相比“小仁政”的“大仁政”)——依靠苏联在朝鲜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所可能提供的工业化援助,在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中为工业化与现代国防争取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保障与民族独立——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基础与治理结构采取影响至今的“激进化”改造④。对于这段特殊历史,不应认同于割裂对立的主流叙述和今人视角的简单评判,而应放回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脉络中进行理解。且不说全球范围内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激进,对于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身处必须以工业化为生存保障和基本条件的全球“丛林法则”,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⑤但仍需清醒意识到,该时期对“三农”所进行的巨额提取及其为国家“工业化”与各种危机化解做出的重大贡献(温铁军等,2013),而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将产生高昂的制度成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虽然政治意义上的“激进”思潮与实践似乎给“三农”松绑了,但经济上的“激进”改革却让“三农”在“市场化、全球化、非农化”的时代强音中承受着隐蔽却更具规模的成本与代价,并最终以世纪末的“三农”问题为表现而集中爆发。
回顾百年历史进程,不应仅从中国内部或主观层面进行思考,还需充分联系特殊时空条件下的外部宏观环境——在这个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所谓的“极端的年代”里,资本主义的成本和代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作为基本事实,随着1929—1933年西方大萧条与民国白银危机而加剧放大;两场世界大战所掀开的“热战—冷战—后冷战”格局为深度卷入其中的每个“竞争单元”提供着普遍激进化的不竭动力。身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和“激进”结构之中的中国,其“独特性”不再明显与有效,这既是梁漱溟和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争论的背景,也是本文讨论“百年乡村建设”的动力和张力所在。
(三)重思“激进”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需要把“激进”放回百年历史进程,并从政治、文化、经济、生态等维度进行整体性检视。如果具体到以“三农”为视角,“激进”不仅涉及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变革及新自由主义主张下的改革实践,也包括因忽视各种现实条件与弱势群体利益而强势推进的全面都市化、不顾乡土社会特点而简单照搬的高成本现代治理、为“三农”危机转嫁而合理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包括以农村发展为目标但受此意识形态影响而深陷其中的某些NGO实践。
导致这种整体性激进的原因,不仅包括百年屈辱与民族情感所引发的集体焦虑、外来激进思潮的某种中国版实践,同时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坐标参照下因经济基础差距而对上层建筑“倒逼”,进而产生的“去脉络”(脱离适当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效果。具体说来,乡建视野下的“激进”主要指不顾资源禀赋、社会条件、文明形态和生态制约等国情,强势且大规模推动以“工业化、都市化、非农化”为特征的社会变革,既导致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整体性危机,又使多元可能性和丰富性受到遮蔽与消解。
然而,这种“激进”也不可能是线性单向和一帆风顺的,在不同层面上一直充满张力,各种被“遮蔽”的面向也常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再现⑥。这让“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既互为因果,又充满曲折与悖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展开的基本脉络。
三、百年乡村破坏:激进化的后果与动力
“百年激进”及所产生的实践行动对中国产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影响。“百年乡村破坏”作为其在“三农”层面上的后果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进一步“激进”的条件与动力。此说法可追溯自梁漱溟70多年前那个振聋发聩的总结:“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2005:481)。作为进一步的辨别和说明,他解释道:“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梁漱溟,2005:152-154)。
本文借助这个归纳,泛指近代中国乡村的某种整体性趋势与状态,希望突出其中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同样作为整体视野下的把握与批判性归纳,“三农”问题可以理解为“百年乡村破坏”的当代表达。此论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⑦,至今已为学界及政策制定部门所共知。它强调不只存在着经济维度的农业问题,而应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立体维度看到“农民、农村、农业”的整体存在。它不只与“农”有关,而且联系着宏观问题与外部制度环境,与乡村整体性破坏与社会结构显著变化联系在一起,一般会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温铁军,2009:6、51)。
若以中国为例,近代以来农村的衰退几乎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在不能进行外部殖民的情况下,面对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一难以逾越的壁垒,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的“无奈之举”和“真实经验”。在此格局下,越是在资源短缺条件下快速形成工业化,其由弱势群体和“三农”所承担的“代价”⑧就越大——那绝非一次性的“创业成本”,而是需要持续不断且叠加递增地加以“偿还”,进而引发更为深刻的整体性危机。所谓“三农”问题,作为“百年激进”历史进程的内在产物与逻辑必然,与其说是“农”自身存在问题,不如说是“百年激进”的推进将其变成“问题”。
为了全面认识“百年乡村破坏”的表现、成因与影响,下文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切入,希望指出其与“百年激进”相互引发:“激进”导致“乡村破坏”,而“乡村破坏”的残酷事实又产生着进一步“激进化”的社会基础。
(一)“三要素”的多形式外流
现有关于激进的讨论多聚焦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对于“三农”来说,应特别关注“经济激进主义”。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三农”困境并非限于地租剥夺⑨与外敌侵略,其影响也不是一般的农民破产或农业凋敝,百年来不同形态的力量以各种目的和名义从“三农”提取资源,外加工商资本和现代金融对小农与乡土社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剥夺,整体导致“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的多形式外流与各种依赖(许纪霖、陈达凯,1995:178-182)。
回到民国历史脉络,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面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压力(陈翰笙,1941),并受市场和权力双重支配及兵匪横行、战乱频繁等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适应于工业化和都市化需要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村经济货币化加深,小农户生产和生活收支的现金比重增加,生产结构出现大范围的“被动”调整,许多经济作物开始出现,种植结构日趋专业化与区域化,对于分散小农来说则是大幅提高了各种风险,同时加剧了分化(黄宗智,2000:141);另一方面,由于改变了以往的租地模式,租赁农场、富农经济成为普遍现象,地主经济发生向工商业方向的实质性转变⑩,外加金融化对小农与底层社会的新的剥夺(黄宗智,2000;温铁军,2009)。由此导致农业剩余及稀缺“三要素”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农村劳动力则随着农户破产而不断逃离农村,农村经济因此凋敝。与此同时,高利贷金融资本以及产业资本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它们打垮了小农,更导致盗匪横行,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所维持的乡村稳态结构随之彻底破坏。
对于自近代以来已逐步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这种“三要素”外流还直接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正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加速之际,出现了西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邻为壑的危机转嫁,对中国经济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全国出口衰减,物价惨跌,市场萧条,工业萎缩,农产滞销,农业亏损,农村金融枯竭,农民加速贫困破产”(刘克祥、吴太昌,2010:25),这些都严重阻遏了民国年间的“黄金十年”。当美国金融利益出于自保而提高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中国作为刚刚兴起工业化的“银本位”国家立即出现白银大量外流,迫使政府于1935年放弃白银币制改行“法币制”。由于城市积聚资本促进市场经济的同时也集中了外部性风险,这个本应由都市承担的危机又进一步向农村转嫁,加剧了土地兼并、小农破产与社会动荡。11
这种“三要素”的单向外流也是当代“三农”问题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除了一般的资源外流外,留守问题突显也是当前乡村劳动力外流的严重后果。乡村金融“存易贷难”的结构困境则反映出一般的现代金融难以服务真正的乡土社会。土地虽然无法“流动”,但当前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下各种“就地转换”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非农化”影响。
这种“外流”虽然为主导性趋势,却并非绝对,也不是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同样催生出多样化的改良实践,也即下文所讨论的广义乡村建设,在事实上呈现着“外流”与“回流”混合发生与紧密互动的复杂局面。
(二)稳态乡村秩序的改变
“百年乡村破坏”作为中国乡村的整体性困境,不仅源自和表现于经济层面,其深远影响同时体现在社会与政治层面。
梁漱溟认识到“秩序”问题是“百年乡村破坏”的重要方面。如果说这种整体性“失序”在上层政治中表现为军阀混战和吏制恶化,那么就乡土社会来说,则体现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盗匪横行与乡土社会普遍“劣绅化”12,传统乡土社会治理中相对低成本秩序的解体及乡土保护性力量的式微与失效,还包括“法治/警治”等现代治理方式因高成本13而难以真正“下乡”,或者在推行过程中因水土不服而发生变异。
在杜赞奇(2003)的研究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导致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膨胀的庞大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进而导致“劣绅驱逐良绅”。黄宗智(2000:256)则指出,20世纪村庄共同体结合力因小农半无产化而瓦解,且随着外来压力的增加,导致原有政治结构的崩溃以及权力的真空,造成恶霸、暴徒乘机崛起的局面。张鸣(2001:3-5)认为其还导致“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全力挤压和侵蚀,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
也即,无论是为了提取更多包括人力和军费在内的各种资源,还是为了国家政权建设所需完成对基层的进一步控制,此前长期维持乡村基层稳定且相对低成本的治理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乡村建设兴起的背景和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熟悉乡土脉络及其内在机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通过“内向型”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进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过度)组织农民、动员乡村和提取农业的做法,但也充分尊重基层与群众的创造,促进包括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另外途径向乡村“回流”,多形式推进“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其中很多实践因密切联系群众并与乡土脉络互动充分,具有低成本、创新性与“去激进化”的特点。相比之下,改革开放虽然让农民个体致富,但乡村却因不断“去组织化”而降低了对城市与外部资本剥夺的抵抗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部宏观环境和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变化,使这种“掐草尖”式的剥夺进一步加剧且合理化,留给乡村的是数亿“原子化”的留守群体(儿童、老人和妇女),以及越来越难以组织、凝聚起来的名义社区。
(三)“乡/土”作为问题与对象
随着“百年激进”对乡村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影响与社会重构,城乡二元对立成为影响深远的普遍格局,“乡/土”的功能和内涵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乡村与农业所应有的“多功能性”14日益被遮蔽,乡村也从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的多元空间被窄化为各种资源的提取单位与危机载体。另一方面,面对剧烈的外部压力与生存刺激,在“百年激进”所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导下,“乡/土”常在工业化坐标与竞争逻辑中“败”下阵来,在逆推中自认“落后”,在追赶中日益“问题化”。在现代性所带来“都市眼光”的寻视下,一直以来作为正面象征的乡村在20世纪转趋负面,本不是“问题”的乡村在现代成为“问题”(梁心,2012:12-13)。也可以说,当“百年激进”进程以都市为主导并确定了特定的“意义系统”后,以农业文明(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5等)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因难以分享主流坐标下的“意义”而日益空洞化,乡村则处于“非现代”和“反现代”的相对位置而被不断边缘化16。
这种“问题化”后的“乡/土”既在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不平等与割裂对立,又循环生产出一整套让农民无法自信、让农业失去尊严、让农村难以安身立命并获得意义、以都市和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化。这些不仅成为外部主体对乡村简单而又刻板的定型化想象,更作为“社会共识”内化为农民或乡村工作者的自我认知与困惑源泉。
如果说“问题化”让“乡/土”进一步成了问题,“对象化”则让这种“问题”进一步定型且难以真正面对。成为“问题”和“对象”之后的“乡/土”虽因突显了“乡土”困境而引发更多的关注与行动,但也强化了主客对立的人为二分,使得知识分子或具有“话语权”的人(无论是否来自乡间或从事乡村相关工作17)不自觉地疏离于“乡/土”脉络,在“文明-愚昧”、“进步-落后”、“主动-被动”、“救-被救”、“上-下”等隐蔽偏见中迷失。“对象化”所带来的“他者化”虽然让“问题”和“问题之人”似乎清晰可见,但也将问题本质化和静态化,降低了透过历史脉络和时代张力以自我反省与实践行动的可能,参与构成了进一步“激进化”的土壤与动力。实际上,它作为“百年乡村破坏”之常被忽略与遮蔽的重要面向,恰是其对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有效配合,使激进改造具有不可质疑的合理性,并使权衡之下的可能“成本/代价”获得某种谅解。
四、作为回应与探索的百年乡村建设
如前所述,“百年激进”成为特定时代的主导性趋势,并从不同层面上引发“百年乡村破坏”这一历史性进程。然而,当这种“输入型”激进和社会理想在现实层面落地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后,则充满裂隙并引发了多种可能性。特别对于中国的“三农”来说,其绝不只是“问题化”与“都市眼光”之后的诸多“问题”,本身也正是宝贵的力量源泉(如晏阳初从在法华工身上发现“脑矿”进而终其一生推动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与中国的有形之“根”(如梁漱溟深思熟虑且深入一线实践后的归纳和坚持)。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形态和独特国情的厚重基础,也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土壤与动力。
(一)“三农”辩证法
在资本主义及各种“激进”论述中,“三农”问题的安置与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恩格斯(1971:299)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时的生产方式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c Mcisncr)则归纳道:“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史的舞台是城市,而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城市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史这一概念中,农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还是反面角色”(迈斯纳,2005:27)。同时他还引述列宁的观点:“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迈斯纳,2005:39)。此外,许多论述也常将“农民”排斥于历史动力之外18,常见处理是为其派定某种特定的边缘化位置,通过“落后/牺牲品”(迈斯纳,2005:27)这样的模糊指称与“他者”身份,以对真正的问题完成某种转移与置换。
可是农业毕竟作为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所以在原有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框架下能够“自圆其说”,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外部殖民与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以转移生产压力、成本及过剩人口——“以空间换取时间”,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化学农业、石油农业与生物农业所带来的新增长——“以时间换取空间”。然而,如此“外部化”与“透支未来”的做法势必引起承担代价群体或自觉秉持草根生态立场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抵抗,“能源/环境/生态/金融/人类安全”等各种危机正日益构成时人的日常经验。
正是这种“三农”辩证法孕育了广义的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其具体源起可能不同,既可能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归纳四个层面中的一个或多个(“乡村自救”、“乡村破坏而激起救济乡村”、“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面对千年社会组织已崩但新者未立时,重建社会构造”),也可能对应着梁先生思想深处对“人性自觉”的坚信,还可能如当代乡村建设新归纳的“遮蔽”之“再现”19。
“百年乡村建设”作为对“百年激进”和“百年乡村破坏”的回应与另类探索,以乡土、国情、生态为视角和立场,尝试改出“激进”思路对乡土社会的脉络偏移,并减少其负面影响。然而,这种回应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简单的“冲击-回应”,因为“他毁”和“自毁”常彼此引发,“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互为因果,乡村建设既包括对冲击的回应,也包括对“其他回应”的回应,以及二元框架外新可能空间的探寻。与此同时,整体性的“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则在现实中参与构成了乡村建设的脉络背景、社会土壤与影响因素。
也可以说,现实层面的“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一直在辩证性地动态存在着,前述之“三要素外流”、“乡村秩序改变”、“乡土作为问题与对象”虽为大势所趋,但也并非绝对性效果或单一化过程。“激进化”推进的同时,也召唤“社会自我保护”20与形式多样的“另类实践”,这些力量作为一种现实回应与历史存在,构成并孕育了更为广泛多样的乡村建设实践。
因此,三个“百年”并非简单的因果反应21。一方面,建设性实践和自觉反思的存在影响并制约了乡村破坏的程度与深度;另一方面,正因为有着包括乡村建设在内多元化力量的质疑和挑战,百年来的“激进化”进程才曲折、反复且充满裂隙与开放的可能。三者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进程。
(二)不只建设乡村的乡村建设
正如上文分析,如果运用脉络化的整体视野与去意识形态化分析,中国乡村建设的兴起与展开不是简单的微观个案或个体行为,而直接联系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正如梁漱溟(2005:161-162)所指:“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乡村建设的推动者可能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重主体,内容也常因各阶段不同的问题与现实需求而充满差异,方式和载体更是灵活多样。但回到三个“百年”的背景脉络中,却有着共同的内涵,如若相对于前述“百年乡村破坏”中的三个层次,则主要体现为:在经济上促进“三要素”的回流;在社会上回嵌22“乡/土”脉络,重建有利于乡土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秩序;在文化观念上打破意识形态化的刻板认识与二元对立,在新的坐标下重新发现“乡/土”价值,以此打开进一步的实践空间与多元可能。
如前所述,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反应性和保护性的多元化实践,在一线行动中经常表现出分散与多样性,相对于强调“根本性”和“总体性”的变革来说,常被研究者和观察者归结为“改良”,且乡村建设实践者也愿意以此表达自己的主张、思考与立场,并希望以这种“去激进化”的态度区别于主流。然而,这种立足底层与乡土社会、强调民众参与和建设性实践的“乡建式改良”,与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各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保守思潮存在着较大的不同:看似零散温和的乡村建设在微观实践中也有着视角独特的宏观视野23与一针见血的现实批判(如对现代教育、精英倾向、发展模式等),并通过乡土性来进一步明确中国性。它强调建设,但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乡土社会与低成本良性秩序建立的各类努力。对于不利于“三农”的各种消极力量,则努力进行最大可能的转化,虽然这个过程中充满策略性妥协与失败。同时,这种“改良”不等同于“改良主义”,它随着外部环境与历史脉络变化而变化24,所坚持的包容性除体现着实践者在“激进化”过程中的“不忍之心”,还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包容的思维,更基于晚清民国以来充分的现实历史教训——各种激进对抗和二元对立的最终收益往往被精英利益集团所获取,代价却多由乡土社会与弱势群体承担。
进一步看,兼顾“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功能的乡村建设既不同于主流框架与激进逻辑下的逃避或回归,也不同于一般的消极“防卫”,而内涵着积极建设、开拓创新及对各种主流的质疑批判。当然,“另类”与“主流”也不是二元思维下的简单对立与割裂,本身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激进”虽已百年,但相对于人类漫长历史只是短暂瞬间。已有研究指出,乡村建设内在于中国更悠久的历史脉络中,无论是先秦思想的渊源追溯(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2011),或是泰州学派精神世界的连接呼应(宣朝庆,2010),还是北宋乡约的直接影响(曹锦清,2006),都远比近现代长久。本文之所以希望以“百年”为时段,并将清末设定为乡村建设的实质性起点,重点在于强调近代以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和“百年乡村建设”这三个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相关。也只有突破对乡村建设以“十年”为单位(“民国十年”加“当代十年”)的常见设定,才能由此打开一个新的反思空间。也可以说,乡村建设既是近代以来有着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又是超越近代而内在于中国更长时段历史脉络之中,有着更为广泛资源构成的乡村民间民众建设史。
(三)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村建设并非始于常见论述中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乡建派”25为代表,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改造实践,而是发轫于更早的清末民初。甲午之后整体性的“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引发并联系着一场以底层和乡土社会为主要空间的建设性实践。所涉主体、方式、内容多样,既有外来知识分子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异地实践”,也有由乡土社会自发、本地良绅主导、兼顾以“乡村自救”与“社会建设”为目的之“在地行动”,还包括1949年至今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从整体上说,它包括前后呼应的三波乡村建设。26
第一波乡村建设以“官民(间)合作”为特点,起于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良绅之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具有自觉性的“自下而上”式社会改良;兴于20世纪20年代外部混乱的军阀割据环境难以改观的局面之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27;衰于国民党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导致乡土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迁往重庆之后参与北碚试验,兴办乡建教育与华西试验区;被替代于1949年共产党国家力量的全面建设。
其中,190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民间乡村建设实践元年。该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米鉴三)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董,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积极开展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乡村自治。1914年时任定县知事的孙发绪看到翟城村学务发达,风俗良善,于是提出效仿日本,创办中国的自治模范村。其提议得到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米迪刚(米春明之子)的高度赞同,并联合其他乡绅着手办理。经过多年探索与建设,定县据翟城村经验制定全县村治大纲,广为推行,而孙发绪因村治有功,擢升为山西省长并在山西推动乡村自治(王景新、鲁可荣、刘重来,2013:270-275)。这段暂未引起充分研究与讨论的本地乡绅之“翟城试验”,直接引发了后来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外来知识分子推进之“定县试验”,由此翟城村也开启了近代史上多样化的百年乡建实践。
作为早期乡村建设的另一个代表性实践,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建设,已有学者总结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28。这一由“状元改行”所推动的地方性建设有着甲午战败的刺激,同时和“翟城村治”一样皆属清末新政释放实践空间后的历史产物。其“工农并进”、“父教育、母实业”等建设思路及所取得的成效,可以为此后“以农立国-以工立国”、“保守-激进”等讨论提供不一样的例证。
这波乡村建设涉及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种实践,学界已有较丰富的描述与研究,此处不做重复。
紧接着的第二波乡村建设由全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在官方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由“官方主导”,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相对于民国时期第一波乡村建设来说,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进行全面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29。这虽然使“乡建派”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和中止,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水利建设、互助合作和各种实践创新(如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等),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到了集体化阶段,由于随之伴生的国家力量全面进入“三农”以获取剩余投入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乡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业化的优先需求与乡建初衷背离。即便如此,乡村建设也无声地存在于因千差万别而难以充分集权的广大乡土社会,草根民众仍然为稳定乡村、维护传统做出了艰辛努力。
进入80年代,由于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发展与基层治理问题,而包产到户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之后,则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等问题。于是在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1987—1997年间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其与自50年代开始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一脉相承,最后衰于90年代以来的宏观环境变化及东亚金融危机。
第三波乡村建设于2000年起持续至今30,以“官民互动”为特点,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和“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兴于新农村建设,转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对乡土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破坏。
经过“激进”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于彻底纳入全球化,各种利益集团进一步结合,将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成本向乡土社会转嫁。第一波乡村建设源起时“乡村自救”、“救济乡村”、“社会建设”等多层面因素与条件重新具备,集中式的乡村建设因此再次“显化”。第三波乡村建设由民间力量率先引领,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其中,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发展出包括“学生下乡、教育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农业、城乡融合”、“大众参与、文化复兴”在内的当代乡村建设五大体系(潘家恩、张兰英、钟芳,2014)。
这波乡村建设在“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与民间立场上,与第一波乡村建设有较大的相似性31,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张力。一方面,面对着全球化大潮的深刻影响和高速城市化的巨大“拉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政府下乡与“精英俘获”而愈益突出的内卷化机制作用,乡土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剩余越来越少。在此情况下,农民自主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建设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代乡村建设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例如,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原来是推动“激进”现代化的,但因“生产过剩”的出现及各种结构性危机(环境、能源等)的制约,而使得某种“倒逼”下的“反思”和以“反思”为包装的新一轮利益圈占同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自我区隔于底层与“三农”,但当其切身感受到包括食品危机、雾霾、城市高房价等在内的伤害与压力时,也产生了参与乡村复兴的可能性。
也可以说,第三波乡村建设在实践中面对着来自附庸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更大的压力、竞争与诱惑。正因如此,其在实践中不限于“乡”与“土”,而动员包括市民、文化人等在内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与跨界参与;除传统的实践外,还开展包括全球化挑战下的第三世界的经验比较,并与发展批判、文化反思、话语建设等多领域的工作结合,其面向与涉及范围也更加广泛。
五、小结
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指出:
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凌辱、压迫的过程中,由于受外部冲击和直接侵略而导致资源外流、生存危机与竞争焦虑,进而引发了包括“自强”和“自救”在内的复杂实践与各种不期然的客观效果。如果以“三农”为视角,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部分国人从各层面所进行的“激进”努力,常以“内生性”工业化的方式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代价和成本,制度化地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不断地产生着中国式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甚至形成了乡村的致贫、致乱和致害效应。正是这种偏离本土、乡土与国情脉络(也即梁漱溟所强调中国之“特殊性”)的“百年激进”及相应的单一化社会共识,对乡村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整体性导致“百年乡村破坏”。
然而,广大乡土社会和弱势群体也要生存和“活着”。如何生存?它不能简单依靠对抗或反对32。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着“激进性”,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更为其在实践中日益显现的矛盾与困境埋下了伏笔。
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回应着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是农业人口大国的“三农”因“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以及在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解体的双重影响下,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可能的持续努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虽然国人有着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但如何在一个“精英、二元、线性”的叙述框架下重新发掘被以“成王败寇”、“好人好事”、“就事论事”等常见做法所遮蔽和“简单化”、“浪漫化”的乡建事实,如何在“革命史”与“现代化”夹缝中让乡村的民间民众建设史进一步释放出更大的启示空间,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曹锦清,2006,《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重温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载《探索与争鸣》第10期。
陈翰笙,1941,《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载《中国农村》第7卷第3期,收入《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城山智子,2010,《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秋珍,2007,《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19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高宁、胡迅,2012,《基于多功能农业理论的都市农业公园规划设计——以莫干山红枫农业公园为例》,载《南方建筑》第5期。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质疑全球化》,载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姜义华、陈炎,2000,《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梁漱溟,2005,《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心,2012,《都市眼中的乡村: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林卿,2012,《中国多功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思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 期。
林毓生,2006,《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2010,《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罗志田,2014,《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迈斯纳,2005,《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潘家恩,2015,《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载《读书》第4期。
潘家恩、杜洁、钟芳,2014,《发展幻象的裂隙与社会化农业的兴起——以北京L市民农园为例》,载《青年研究》第5期。
潘家恩、温铁军,2012,《“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第3期。
潘家恩、张兰英、钟芳,2014,《不只建设乡村:当代乡村建设的内容与原则》,载《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
王景新、鲁可荣、刘重来,2013,《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2011,《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铁军,2009,《“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温铁军,2006,《新农村建设与城乡和谐社会》,载温铁军(主编):《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北京:文津出版社。
温铁军,2004,《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温铁军等,2013,《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
吴志峰,2008,《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叙事——知青文学(1966—1986)研究》,载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萧功秦,1999,《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
许纪霖,2000,《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1995,《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
宣朝庆,2010,《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北京:中华书局。
杨念群,2001,《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余英时,2006,《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张鸣,2001,《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赵旭东,2008,《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郑大华,2000,《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立,2010,《极化的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
注释:
①实际上,“激进”所强调之“整体性”同样体现于资本主义的各种运作中。正如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318、321)所指:之所以我们显得渺小,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笼罩在某个庞然大物即资本主义之下;作者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通过政治、经济方面得以显示,还通过其充满“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的话语,使其构成资本主义这个“不能改革的改革对象”。在这个逻辑下各种局部的、片面的改革终归是脆弱无力的,都将被资本主义以另一种规模或者另一种程度的努力所抵消。
②罗志田(2014:1)认为,实际上是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
③比如,朝鲜战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参见温铁军(2009)。
④乡土社会复杂多样且具有强大的包容和化解外部“激进”实践的能力,而对于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与外来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成功的独特性之一就是能够紧扣乡土脉络,本身也非铁板一块。回到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执政党既从国家脉络和工业化角度“去(乡土)脉络”,又在实践中大规模推行“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进而构成复杂且充满张力的现实状态。
⑤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且奉行“赢家通吃”的20世纪全球舞台,从被侵略国家的民族利益及国防安全来说工业化无疑是必要和必须的。事实上,在百年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无论农民、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对这种意义上的全民“奉献/牺牲”以实际行动进行了支持,并成功构筑了今天中国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然而,问题在于由此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及派生出由强势部门或局部利益集团以“国家/整体”为名义的进一步剥夺、转嫁与合理化。
⑥比如农业的多功能性与社会性,虽然在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强势影响下一度被“遮蔽”,但随着食品危机、城市困境的加剧及生态限制之存在而“再现”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可参见潘家恩、杜洁、钟芳:《发展幻象的裂隙与社会化农业的兴起——以北京L市民农园为例》,载《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⑦温铁军认为,“三农问题”本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纳入全球化、造成宏观制度环境恶化、导致乡土社会衰败趋势之下我们抛出的一个标签,标志着我们在官方主办的“农村改革试验区”10年总结中形成的主要思想成果:对外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派生全球化强加于中国乡土社会,造成邯郸学步与普世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政策思想的批判。由此既对附庸于全球资本化的政策主流回归本土需求产生影响(确实部分地起到了政策调整作用,如中央政府以“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取代单纯的农业问题、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投资和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获得了新世纪以来第三波乡村建设重新启动的机会与空间。
⑧此处对代价和成本的强调,不同于一般从既得利益出发,以“代价论”来实现对现状的辩护。它更多针对当前主流经济学“只谈收益不谈成本”与“隐蔽代价”这一现实。此外,它也不应在一般框架下被处理为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好坏对错,否则将是另一种简单化,而需放回具体历史脉络中。
⑨温铁军曾指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小农经济自给能力下降和收入的货币化。这四个重大变化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从本质上看,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必然出现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即“三农”的外部环境是农业衰败的主要原因(温铁军,2009:95、128、137-138)。
⑩地主迅速从“在乡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他们更重视在外的工商业收益,农村收租则由以前的“秋后租”、“分成租”变为“春前租”和“定额租”。对那些租地耕种的农户,以前可以用收获的农作物或以佣工形式支付的地租,现在必须以货币形式交纳。
11日本学者城山智子(2010)通过对该时期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研究指出,大萧条期间国际银价的巨大波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并将其货币贬值,其他国家随后跟进,日本于1931年12月、美国于1933年3月相继放弃金本位。根据这些国家的货币衡量的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汇率也就随之上涨。中国的工业丧失了从前的低汇率优势而不得不向外出口白银以弥补逆差。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进一步提高了国际银价,正是这种价格空间刺激了白银从中国大规模出口。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具体到对乡村的影响,1929年之前,在收获季节城市资金通过购买农产品流向农村,但是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进而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后中国原材料价格随之下跌,资金向中心城市流动,外加匪患引发的不安全导致农村地区白银进一步外流,现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原来还能发挥作用的民间自发互助金融在外部经济压力和持续萧条下逐步失效,农村地区因而遭遇现金和信贷的双重短缺。在此背景下,农村家庭发现维持生活变得极其困难(据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统计数据》[1937]在调查十县后指出,51.5%的农民家庭负债,转引自城山智子[2010])。1931年以后,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于全球萧条之下。
12杜赞奇(2003:114-115)结合“满铁”的原始资料指出: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性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对此成因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比如罗志田(2014:108)认为: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是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读书人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
13如黄宗智(2000:284-285)结合“满铁”资料指出:“地方政权机器的扩张,加重了县政府的开销,从而提高了它们对村庄在赋税方面的要求。而税额的提高,又意味着扩大税收机器的必要。……河北的顺义县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1931年,县政府几乎用一半的经费来维持警察和保卫团。”
14虽然概念意义上的“多功能农业”1988年才出现(高宁、胡迅,2012:82),但却被认为是“农业本质特征”(林卿,2012:19)。农业除了生产功能外,还具有文化教育、农村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等非商品产出相关的环境和社会功能(陈秋珍,2007:71;周立,2010:101)。除农业外,乡村也具有“多功能性”,近年来当代乡村建设在城乡互动和爱故乡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就是例证。
15如罗志田(2014:32 )所指,西方输入的使命感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石穿的渐进功夫。
16恰是这种“想象中的‘他者’,正好维持着人们对现代城市各种缺陷的容忍。城市和乡村在现实中的对立与在文化现象中的补充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吴志峰,2008:454)。
17即便政治立场和对乡土的认识不同,包括乡建实践者和共产党在内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问题乡村”倾向。前者如晏阳初思想中潜在的“启蒙”意识(详见赵旭东[2008]、梁心[2012]),后者如共产党在农民动员和乡村改造中的阶级论述。但当这些认识具体到实践时,又都充满复杂性和动态性。
18即使在毕生献身乡村的晏阳初先生那里,也充满不无贬义的“愚、穷、弱、私”式归纳。随着实践的深入及来自乡土的改造,这种看法得到了调整,见潘家恩、温铁军(2012)。而对于当下中国语境,农民要么成为革命的动员对象,要么只是革命成功后的“牺牲者/被‘骗’者”……总之,他们一直都是被命名或指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文化影响,类似的刻板化定见已逐步内化为被叙述者的某种自我认同。
19如当代乡建中的社会生态农业之兴起,除一般条件外,还可以理解为农业本身所具有的“多功能性”长期受到城市化与“非农化”遮蔽,但随着生态危机和城市病等各种新因素的出现,曾经的“自圆其说”捉襟见肘,进而导致“多功能性”的再现与丰富实践空间的重新打开,见潘家恩、杜洁、钟芳(2014)。
20此概念为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之核心概念。通过对百年历史的宏观分析,他认为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而表现各异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其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反向运动”也同样存在着。它可能包括人的反抗——劳工运动、自然的反抗——农业人口的土地保护运动和现代的绿色运动、金钱的反抗——经济的周期波动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等。如此“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原著对20世纪中叶诸多世界议题的讨论,也有助于我们对百年中国“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的重新理解。
21不是一定要到二三十年代乡村全面破坏后,集体亮相后的乡建才是乡建,事实上也有先知先觉和引领潮流者,如张謇在甲午后就开始了建设性实践并持续数十年,虽然其未在名义上使用“乡村建设”一词。
22此概念相对于卡尔•波兰尼的“脱嵌”而言,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3比如,梁漱溟有着包括本文所引述观点在内的各种宏观分析,其给《乡村建设理论》则取“中国民族之前途”如此“大”的副标题。晏阳初虽然做的事情常显微观,但也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总结出包括“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救济,而是发扬”等在内的《乡村建设十大信条》。虽可能因角度不同,其宏观性未必得到认可,但我们不要简单化地仅从技术层面对乡村建设进行理解与判定。
24比如,当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救亡压力,多数乡建实践从“救民”向“救国”转型,并以宣传动员、
政治调停、人才培养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抗战救国和更广义的乡建实践。此时各乡村建设团体领导者也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整个民族和生存意义上更大的自我保护。比如,梁漱溟参与创办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间艰辛斡旋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作孚在抗日战争最紧张、最危急的历史关头组织了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之“宜昌大撤退”,陶行知发起了志愿兵运动与难童教育,晏阳初利用国内外影响积极宣传抗战等。
25需要说明的是,同一乡建派别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即使同一人的思想和主张也随着外部环境及实践推进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各乡建团体骨干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和交叉,所以实际上不好做出“✕✕派”这样的清晰区分与定位。
26部分内容引自潘家恩:《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载《读书》2015年第4期。
27乡村建设集中呈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其与民国大局甫定、各地名义上归于大一统有关。面对清末民初的四分五裂,通过军阀之间的多次局部战争重新形成了大一统国家之后,亟需建立国家稳定的局面,否则不可能追求现代化。但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又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必须从乡土社会提取剩余,一定会使乡土社会的“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经济基础不断衰败和民国政府在乡村建立政权、稳定社会的政治要求之间,发生了几乎对立性的矛盾。这给当时立意爱国并希望坐言起行的知识分子难得的实践空间。
28它与二三十年代乡建实践在内容上多有交叉,通过当地城乡建设给平民带来“三要素”回流的效果。其在创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时所坚持“实业的社会性”或创建早期中国本土化的“社会企业”(与北碚乡村建设领导人卢作孚的理想相似,两者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及由此产生的低成本县级治理等都是乡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
29虽然当时中国进入到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性矛盾仍然存在。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仍然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推动国家主导下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则显得十分必要。
30 2012年12月2日温铁军在西南大学主题演讲《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乡土实践中渐进地认识客观世界》中指出:如果说五十年代政府主导的制度试验(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是通过促使小农经济的高度组织化来承载城市资本与风险高度集中的危机,由此消纳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那么工业化完成之后政府推进大包干的“去组织化”再度恢复了分散小农经济,则是这种制度承载危机,致使成本过高,政府不得不退出“三农”的客观结果。这就有了民间乡村建设再起于新世纪的历史机会。
31比如,都自觉区别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精英为立场的各种主流做法并因此面对来自“左/右”的各种批评。
32不能简单说这个“以恶制恶”之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错的——要是说是错的,那大家干脆都放弃,永远被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剥夺。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Pan Jia’e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Wen Tiejun,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sn/2016-09-14/40017.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