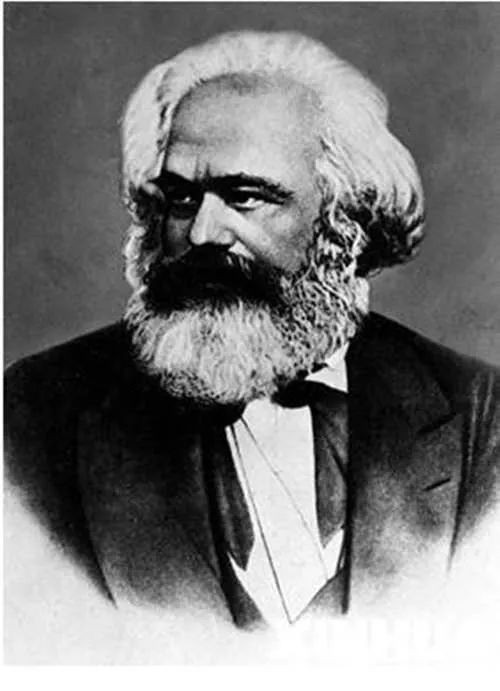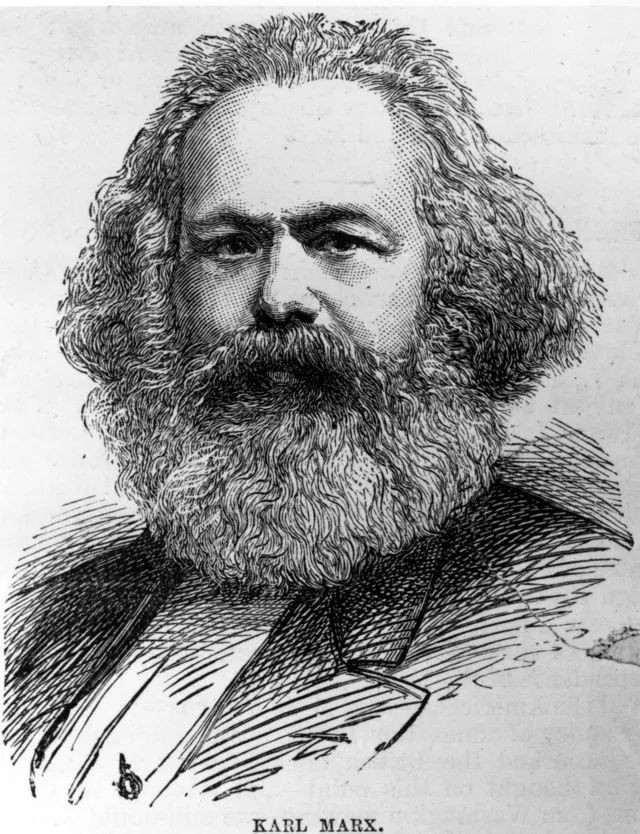董学文:马克思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
摘要: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方法论。他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传统文化始终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辩证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一根主线。马克思思考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恢复唯物论、拯救辩证法、创建唯物史观和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反对任何虚无主义作风、庸俗化的态度和形而上学做法。要重视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所面对的传统文化丰赡而复杂,他对待这些传统文化的态度富有个性,极为灵活,秉持的方法论也极其鲜明。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论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词,那就是“辩证批判”,或称“创新性批判”。也就是说,无论是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平庸乃至低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面对高级的思维成果还是一般的民俗习惯,马克思都是主张通过彻底辩证的批判性分析去加以改造和超越,从而为构建自己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学说服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论述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特点。
01
正确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
重视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任何杰出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思想流派,都会把传统文化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总是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视角来认识某种传统文化的价值,而绝不是仅仅孤立地将其看作一种思想上的闪光点。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1。这段话从大跨度、大视野中告诉了我们传统文化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方面,马克思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他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3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通过比较,马克思看到了传统文化有积极的因素,特别是有时有着现实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功能。马克思说:“对社会状况的批判性论述决不仅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家本身那里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5不难发现,马克思把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到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更为广泛的领域。
理论是要发展的,不会总局限于眼前的形式。而理论的发展,除了实践的推动外,当然要从已有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举例而言,“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6。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先驱”和“前提”两个概念很关键,这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不是从零开始的,它是有先行者(即“先驱”)的;文化的发展也不是无条件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它须有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才能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传统文化,这是人类活动的规律,哪个阶级也不能例外。
02
“批判”是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武器
同样是吸收传统文化,那么马克思有何特殊的地方?或者说马克思的方法论有什么独到之处?我认为,最特殊、最独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始终秉持“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自始至终把改造、转化和超越传统文化作为目的。这是别的思想家所难以达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立场以及由此立场所生发出的思想方法论所决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恩格斯在另一篇文章中谈道:“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8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看待传统文化和思考文化问题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开始他的社会活动,都是生活在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是由前代人创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之中的,他必须在这种给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承中从事活动。而他究竟怎样通过实践来改变社会、改变自身的社会关系,这就形成了他的立场。所以说,立场是一个社会范畴,是由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决定的。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同样如此。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都是为了鲜明表达出无产阶级的看法,或者说是为了自觉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这种鲜明的立场,没有这种亘古未有的理论站位,他们不可能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彻底的“批判”态度,也不可能如此主动地、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前人思想材料。这是我们判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其他思想家在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为何不一样时得出的第一个答案。
马克思明确说过:“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9恩格斯也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而马克思的历史观,“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10。正因如此,他们两位才有勇气和权利宣称:毫不奇怪,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这里的“决裂”,当然不是“决绝”,不是“断裂”,而是为了实现对传统观念改造和变革的“扬弃”和“批判”。“批判”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而且可以说是他们思想方法的本质和理论的灵魂。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讲,他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倘若没有“批判”精神,那就一点儿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也没有了。“批判”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方法论特征的关键词。
03
拯救“辩证法”是马克思“批判”的核心
没有谁会不承认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尽管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批判”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批判”的特点与核心是什么,弄清楚他的这种“批判”到底具有怎样的功能。
我认为,马克思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拯救彻底的——或曰历史的——唯物论,拯救科学的——或曰唯物的——辩证法。它不仅实现了一次方法论的革命,而且极大推动了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进程。为了表述得生动一些,这里不妨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批判”形象地称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3。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是坚定秉持历史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的,是做到了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14。
诚然,马克思不是天生的唯物辩证大师。他是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并改造他们的遗产,经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才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一度是“青年黑格尔”派,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知识界有人全盘否定黑格尔的时候,马克思还是公开承认黑格尔是自己的老师。他曾说:“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他们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15恩格斯同样十分推崇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法,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及革命的方面。他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16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17。恩格斯说:“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18在《反杜林论》“引论”的草稿中,他还写道:“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19这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最高的思维形式”,同时认为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黑格尔,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是相通的。这就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郑重申明: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20,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1
马克思申明,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这是因为,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22,其整个哲学体系描述的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或认识史,所以要把这“倒立着的”辩证法再“倒过来”,实现转化中的发展和发展中的转化。由此观之,除了在“批判”中创立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是没有别的办法能完成拯救“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的任务的。
恩格斯说:“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23请注意这段话里恩格斯的用词,其中透露的方法论信息很多。其一,对传统文化不是要一般地“继承”或“修改”,而是要“批判地克服”;其二,要“制服”对民族精神发展影响大的学说(思想、观念),靠“抛在一旁”或“置之不理”是无济于事的;其三,应该“扬弃”24它,而这种“扬弃”,又是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演化的意义上实现的。“扬弃”就是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5;其四,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这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法论的完整表述。
马克思坚持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在他眼里,“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6。他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27。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论。
04
完成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阐释
马克思汲取并发展了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世纪的精神,以及19世纪初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这条与传统文化打交道的路上,向前跨出几大步,实现了理论飞跃。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费尔巴哈的。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28。马克思还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clair-obscur[朦胧状态]中的。”29恩格斯则说:“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30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受到热烈欢迎:“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31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有严重缺陷的。费尔巴哈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32。马克思则不同,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3。当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对象性”原则设定为“感觉”和“直观”,用“感性对象性”将人类感性实体化的时候,马克思吸收费尔巴哈的合理成分,又把这一原则提升到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更高层次。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4
费尔巴哈曾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35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费尔巴哈的“我与你的统一”,本质上还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自然关系。在现实历史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不过,“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是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36。
针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37恩格斯从旁加边注道:“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3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他们认为“实践”这个中介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39。“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40并指出:“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1在道德论方面,“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2。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突破了整个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中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剔除了其中可能有的神秘或思辨色彩,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历史之间的真实关系。也正是这样,他们才会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3
马克思将“劳动”“生产”“创造”作为人的类本质根据的确证,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所谓“类存在物”的界定,用“异化劳动”理论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为中介,既恢复了唯心主义的生产因素,也恢复了外在存在不依赖于意识的因素,这时候世界的构成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采取了唯物主义的形式而得到复活。”44总之,“正是由于马克思自觉地执着地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才使他迅速地突破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狭隘性,逐渐开辟了一条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线”45。
05
找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根由和依据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46。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同传统文化的关系。恩格斯说:“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47这段话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传统文化——包括这种社会主义学说——是持批判态度的。
的确,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是五花八门的。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面对这些“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些“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的“怯懦的悲叹”,这些“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及“纯粹的演说辞令”,这些“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企图“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的文献,48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拿起“批判”的武器,并表示一定要把他们理论的批判同政治的批判、同实际的斗争结合起来。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建,马克思不得不把自己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上。他打算写一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1845年2月1日,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该书两卷本的出版合同。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留下来一部分,即现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来,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回来从事这项工作。可就是这一次,他也没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关于促使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计划的原因,他在1846年8月1日写给列斯凯的信中写道:“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49用恩格斯的话讲,《神圣家族》这部书“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5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以往批判的历史中,事情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51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提供了契机。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52。因此,为排除思想障碍、躲避观念陷阱、创立理论新说,他们就不能不把“批判”的活动放在首位,从而实现“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53的宏伟愿望。
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54譬如,马克思就曾讲:“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551866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谈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谈到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认为后一本书尽管有些缺点,但“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而且,“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56再如,恩格斯说:“如果只是‘客观地’介绍摩尔根的著作57,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58这些话,从一些侧面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事“批判”活动的依据和理由。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书评时谈道:“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指卡尔·马克思——引者注)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59他还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60这正好说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系现实的品格。
06
通过“批判”将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到新高度
马克思通过“批判”将传统文化改造、提升至新水平,这确实是他理论方法论最出色的地方。马克思“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能“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61这使他的方法论无往而不胜。
马克思在著述中多处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的命运,通过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2马克思这里针对的是黑格尔,批评的是“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因为马克思知道,“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63。
众所周知,黑格尔是把“形而上学”看作哲学基础理论的,而马克思则把它看作是一种思维方法。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64恩格斯则强调:“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65与之相反,“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66。马克思为此还责备蒲鲁东“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67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观和“历史哲学”,所以,他们即使面对消极文化,也能“在一堆糟粕中间可以看到绝妙的东西”68。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黑格尔的著作当然要读。但是,“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构造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69。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布·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的错误言论,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指出了宗教并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政治压迫的表现,必须消除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消灭私有制,消除人的生活本身的异化。马克思在该文中甚至有这样的话:“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70这篇文章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传统文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批判分析,使之对它的认识有质的提升。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一生批判研究最多的领域之一。他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71对其历史了如指掌。在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时,马克思说:“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72并且指出:“李嘉图所以有片面性,是因为他总想证明不同的经济范畴或关系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不是相反地从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这些范畴以及它们的表面上的矛盾,换句话说,去揭示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73可以这样来界定,如果说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明确地站在产业资本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生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李嘉图是克服了亚当·斯密在运用经济学抽象法上的不彻底性,把古典经济学方法的相对科学性充分展现出来的人,那么,马克思就是克服了他们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非历史性和非辩证性的人。
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74恩格斯说得更加形象:“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75马克思正是批判了这匹“笨马”,才诞生了“剩余价值”理论。
07
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这种启示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反对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事实表明,无论是撰写博士论文,还是撰写《哲学的贫困》;无论是对国民经济学著作的解读,还是对人类学著作的评析,马克思对前人的成果——传统的文化和观念——都是充分把握、极其认真研究的。特别是写作《资本论》,他前后花费了40多年的心血,研读、摘录了1000多种相关著述,可以说,马克思反对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传统文化最自觉的继承者和批判者。马克思的理论赢得世界性意义,这与它吸收和改造了数千年人类文明成果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分不开的。
第二,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弄清新文化与旧文化(新理论与旧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是关涉理论如何创新的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应承认“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76;承认新旧理论之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理论创新并不总是一味地向前去捕捉什么,而是往往需要回过头来对旧的东西做出新的改造和转化。“只有通过对旧的东西的理解和超越,才可能有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充分地理解旧的东西,才可能创造新的东西。”77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如果想要在理论上有所超越、有所创新,那就一定要突破原有的观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辩证批判。这种“转化”和“批判”越深刻,对现有文化的认识就越清楚,对未来的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方向也就越明确。没有这种转化性批判和批判性转化的理论创新是靠不住的。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对待传统文化最稳妥的做法,莫过于只进行梳理和阐释。这种意见其实是落入了“过程哲学”78的泥淖。我们应当像马克思那样,表现出巨大的理论主动性和创造性。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照收”,而是“批判”;不是“抛弃”,而是“扬弃”;不是让“死人抓住活人”79,而是要“活人抓住死人”。用马克思的话讲,“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80。以“解放”概念为例,马克思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1。他主张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的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在像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卑微琐事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82。这是马克思针对德国传统文化在态度上的一个忠告。
第三,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坚持辩证思维,坚持辩证的方法论,这样才能超越传统,创新理论,才能得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是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灵魂。我们知道,马克思先是从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做起,一旦剥去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外壳,黑格尔哲学便显露出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不是把人、把事情看作单纯的对象,而是看作活动。正是抓住这一点,马克思便获得了改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契机。如果我们再能不像黑格尔那样去理解劳动,而是像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那样去理解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就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加以掌握。用哲学的话讲,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亦即实践。正是在这儿,让人们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结合点”。这才是马克思在对待传统文化方法论问题上的高明之处。的确,“‘实践’这个结合点的获得,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才得以实现的。一旦建立了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就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发现,有了这个发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有了稳固的基地”83。在“实践”问题上,假如像东欧的“实践派”那样,主张超验的“实践本体论”,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对人来说,实践是一种根本的可能性”84,那就重新回到了费尔巴哈、赫斯等人的哲学洼地,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则是一种误读和曲解。
第四,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坚持阶级分析,深入了解历史的语境和条件。这是马克思给予我们的又一启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描绘得如此高明”,“无与伦比”。为什么能这样?那就是因为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他“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所以,他才能“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85马克思在该书中说:“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86恩格斯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87可见,对历史的了解,坚持阶级分析,使他们洞若观火般地看清了传统文化可能有的作用和功能。
这些启示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向导和指针。
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5 马克思:《珀歇论自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92页。
6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页。
8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2页。
9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页。本文引文中加粗、加着重号处,皆为原文所有,后文不再单独说明。
1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一书的全称,就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9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9页注释89。
1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38页。
1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7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9页。
1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27页。
1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2页。见原编者的注释1。
20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杜林、古·泰·费希纳等人。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2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6页。
24 “扬弃”(英语 sublation;德语 Aufheben)“包含抛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意思,意即辩证的否定。‘扬弃’一词最早见于康德的体系,费希特在著作中也常使用这一词,但多是在该词的否定意义上使用。在黑格尔哲学中,则明确把‘扬弃’作为同时具有否定与肯定双重含义的概念加以使用。他指出:‘扬弃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逻辑学》)这双重意义互相联结,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黑格尔用‘扬弃’来阐明一概念向另一概念的过渡,具有辩证法因素,但是唯心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使用‘扬弃’一词,指的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又使新旧事物联系起来成为有机的整体而向前发展”。参见《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2—1763页。
2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
26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5页。
27 《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1868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8页。
2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同上书,第13页。
29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页。
3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6页。
31 同上,第275页。
3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28页。
3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
34 同上,第196—197页。
3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5页。
3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528页。
38 同上,第528页。
39 同上,第529—53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41 同上。
4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44 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赵鑫珊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9页。
45 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4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9页。
4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86页。
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4—64页。
49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页。
50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
52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2页。
53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同上书,第27页。
5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55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1页。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页。
57 指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5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16页。
59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7页。
60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32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62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6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64 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6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4页。
66 同上,第25页。
67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页。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页。
69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23页。
70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7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页。
7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181页。
73 同上,第164页。
7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99页,注释32。
75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1页。
76 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
77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462页。
78 “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亦称“有机体哲学”或“活动的过程哲学”,是一种主张宇宙是流动的演变过程的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怀特海和美国的哈尔茨霍恩等。“过程哲学”中不乏合理的因素,但其整个体系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参见《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7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81 同上,第527页。
82 同上。
83 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第444页。
84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导论——实践,南斯拉夫的批判社会理论》,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第23页。
85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8—469页。
8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上书,第472页。
8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99—100页。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wh/2023-10-07/84250.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