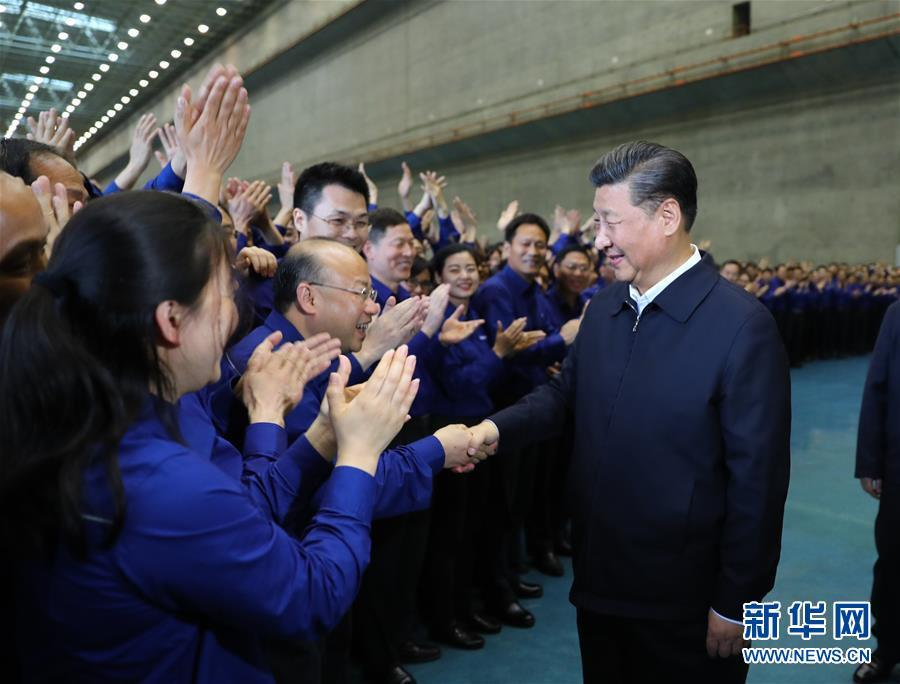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承认”问题——黑格尔“主人奴隶辩证法”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历史渊源
一、问题的由来
《精神现象学》第四章关于主人和奴隶关系的讨论,是学界公认《精神现象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最重要的一段文本,也是引起学界最多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段文本的内容对于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性质来说至为关键,尤其对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传承关系至为关键。一般认为在这个第四章,黑格尔的分析从意识转向自我意识,也就是从对事物的单纯的沉思转向人对自我的生命、欲望、行动和斗争的意识,转向类、他者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从而使黑格尔哲学更加远离认识论态度,而进入以历史精神为主导的存在论态度。这就是一种从马克思实践哲学视角来理解黑格尔的解读路向,它由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卓越解读奠基,是目前影响力很大的一种观点。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美国学者皮平在《黑格尔的观念论》一书中提出,要从康德的先验统觉理论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问题出发来理解黑格尔,他认为由科耶夫阐发的对黑格尔哲学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已成为一种新的教科书教条。皮平指出,正是康德的先验演绎才使得黑格尔创立的主客同一性理论成为可能,其中的关键是康德的统觉或自我意识。在这样的理解方向上,皮平坚持对《精神现象学》最具影响的第四章作知识论解读。他认为,与前三章相比,第四章偏离康德观念论的主题,“突然之间谈起欲望、生命、生死斗争、主人奴隶”,这是“一次猛烈的跳跃”,令人困惑。皮平坚持认为《精神现象学》的中心问题是知识问题,其“一般意图是为绝对观念论辩护”,而第四章引入的人与人相互承认之类的社会关系论题必须以这种观念论为基础来给予解释:“我因此决意主张,正确解读(自我意识)这一部分,不是把它视为全盘转移到社会理论的关注,而是认为此部分更多地是在继续发展‘意识’部分所提出的观念论/客观性论题。”要言之,黑格尔“承认问题”的要义是一个“思想的普遍性问题”:“黑格尔所指的是某种发展的相似心智构成的‘普遍性’论题……主体们开始认识到,真正承认的唯一基础,因而还有自由本身的唯一实现,就在于‘思想的纯粹普遍性’。”①
但是,对《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这种知识论解读并不成功,皮平自己就发现,像这样把相互承认和生死斗争这类社会政治问题“观念化”为“相似心智的普遍构成”问题,既难以理解,也难以在黑格尔的论著中找到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皮平认为,承认论题在第四章的出现是黑格尔的一个难以理解的“戏剧性的视角转换”。
本文认为,承认论题的提出决不是什么戏剧性的跳跃,而恰恰是黑格尔哲学主旨的一次逻辑性凸显。这节很短的文本成为理解黑格尔哲学立场的一个关键,受到众多研究者的特殊重视,决非偶然。黑格尔自己对此作了最有力的说明,他认为,《精神现象学》谈“意识”的前三章只是第四章“自我意识”的诸环节,“到了自我意识我们就进入真理自家的王国”,因为此时便从“对于一个他物的知识”转向“对于自己本身的知识”,这个自己本身就是人自身,黑格尔称之为“自我意识”。按照黑格尔的思路,当人作为“认知的主体”沉思物体的存在时,他只意识到物体的存在而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当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和尊严时,人就是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的基础不是认知而是欲望。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就是欲望,那欲望的对象即是生命。此处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之内涵的如下解释:第一,自我意识的对象不再是某物,而是一个有生命之物:引发我们欲望和激情的自我意识作为对生命的欲望,永远指向在它自身之外的“另一个生命”,因此它是作为“类”而存在:“它自己本身就是类”。第二,一方面,自我意识否定它的对象(即另一个生命),自我意识的内容就是“确信对方的不存在,它肯定不存在本身就是对方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经验到它的对象的独立性:“欲望和由欲望的满足而达到的自己本身的确信是以对象的存在为条件的,为了要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在。”此处黑格尔提出的乃是著名的列维纳斯问题式的一个最重要的经典形式: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不是物体的客观性,而是他人的绝对性,他人的存在是主观性无论如何无法取消的一个绝对事实,用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就是:“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或者用他的另一个更直接的说法:“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明确指出,在《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随着意识发展到自我意识,哲学达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即从专注于某物存在的认识论问题转入以相互承认为中心的社会理论问题:“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②
至此,“在与一个它者的关系中实现自身”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自我意识在否定他的他者的同时又依赖这个他者的存在,因为这个他者不是某物,而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这是自我意识的真正实现,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它自己和它的对方的统一”。③ 这里显示了黑格尔与康德的一个关键性区别:黑格尔的哲学不再是意识哲学,而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其核心问题是承认问题。黑格尔讲,自我意识的最大真理在于它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而承认只能是相互承认:“它们承认它们自己,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地承认着它们自己。”④ 当一个人试图在不承认对方的情况下从对方获得承认时,自我意识的辩证法便终止了,因为只有在对方被承认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能从对方那里实现自己。这就是承认的基本原理,黑格尔用它来表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就它是后来马克思问题的真正起点而言,这还只是一个抽象性的起点;但就它标志着此前康德问题的终结而言,却又具有无比丰富的现实性。
二、重新解读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
现在来看,黑格尔在他所阐述的主人和奴隶辩证法中,作出了哪些重大理论发现。要言之,黑格尔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以抽象的形式正确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本质,即将其理解为在相互依存的前提下为追求相互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生死斗争。这一理解超越传统的善良伦理学,而达至现代社会理论的开端。“生死斗争”这一比喻可以上溯至霍布斯,但只有黑格尔才第一次作出了对其存在论前提的全新理解,即那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相互依存的存在形式”。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依其本性必然与另一个自我意识发生对立和冲突,因为被否定的对方也是一个自我意识:“那第一个自我意识所遇着的对象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像欲望的对象那样,而乃是一个自为地存在着的独立的对象。”⑤ 但黑格尔接着指出,这种对立和冲突的本质却在于,它是人的“类的存在方式”,即斗争和冲突乃是一种相互“为对方而存在”的形式。黑格尔极其深刻地将其描述为,每个自我意识自己的活动同样也是对方的活动。在此处,黑格尔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在相互冲突中相互依存这种“类的存在形式”的精神特性。所谓“自为存在”就是人的存在本身成为该存在者的一种纯粹信念的内容,黑格尔认为这只能实现为“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因为两个自我意识的关系只能是这样:他们必定要进行一场生死斗争,此斗争最终并不指向某种自然对象,而是指向一个精神性的目标:“证明”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追求承认,而此承认又必须依赖于对方的存在,因为基于对方存在的“承认”正是自己的存在被证明的唯一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讲每个人都在做着别人也在做的同一件事情,即追求别人的承认。由于做事的双方总是不等同的,所以承认总是单方面的:一方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只是承认者。“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⑥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作为主人和奴隶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历史。
黑格尔的更非凡之处在于,他揭示了主人和奴隶双方各自包含的自我否定的因素。这一讨论已经进入现代政治理论关于对抗性和压迫的核心问题,并设定了马克思阶级政治的许多议程。先看主人的辩证法。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首先体现为主人的存在状态。黑格尔说,主人的本质就是自为存在,因为主人是为了荣誉不惜冒生命危险去斗争的人,他不在乎自己的自然生命,更重视那种精神性的东西,即被对手承认的荣誉,他因此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主人的荣誉就在于被奴隶承认为主人,主人的自由实现为对奴隶的统治以及由此而来的享乐。这带来的难题是:第一,主人失去与物的直接联系。按黑格尔的分析,主人的支配权就在于:“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主人对于物只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和享用者,而不再经验物的坚实性和独立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主人得到的承认并不是真正的承认。主人冒生命危险是为了得到另一个人(即和他一样的自我意识)的承认,但事实上他仅仅得到一个奴隶的承认,这并不是他期望得到的真正的承认,结果主人并不能实现他为之冒生命危险的目的。黑格尔指出:“正当主人完成其为主人的地方,对于他反而发生了作为一个独立意识所不应有之事,他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反而是一个非独立的意识。因此他所达到的确定性并不是以自为存在为他的真理;他的真理反而是非主要的意识(即奴隶)。”结果是:“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自己所愿意作的反面。”⑦ 科耶夫极为深刻地将这种困境概括为:“主人的地位是一条存在的绝路。”⑧
正是在这个地方,黑格尔过渡到奴隶的辩证法:“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自己所愿意作的反面,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他直接的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⑨ 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奴隶之为奴隶,在于两点:第一是他怕死,第二是他必须劳动。黑格尔认为这恰恰是奴隶“自己返回自己”即重新获得独立性的“两个必要环节”:
(1)怕死这一屈辱特性,在黑格尔看来反而有一种决定奴隶对主人优势的肯定作用。因为正是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奴隶感受到对不存在的焦虑,从而理解了这个存在本身的整体意义。所以黑格尔认为,“对主人的恐惧是智慧的开始”,这种恐惧乃是人的教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奴隶因这恐惧而获得对主人的一种优势,因为主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自为存在”,而实际上奴隶比主人更能理解这种自为存在的意义。
(2)奴隶必须在这种恐惧下为主人服务和劳动,黑格尔认为这种劳动是奴隶对于主人的一种更大优势。首先,劳动的根本特征在于,主观上,它是奴隶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按照一种他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观念进行的;客观上,它是一个通过行动否定和改造给定存在即自然的过程。劳动因此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活动”。黑格尔对此作了精确描述,他认为,主人的享乐作为欲望的满足是一个随即消逝的、缺少客观而持久实质的东西,“与此相反,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⑩ 此外,劳动不仅仅改变事物,而且改变人的存在和本质:劳动具有政治意义,它能彻底改变主人和奴隶的关系。黑格尔揭示劳动的辩证法在于,劳动最初起于对主人的恐惧,但在劳动中,奴隶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他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使自身变为普遍的自我意识和自为存在。按黑格尔的规定,奴隶的这种自为存在实现为他的劳动创造事物存在的“纯粹形式”,“这种纯粹形式被认作弥漫于一切个体的普遍的陶冶事物的力量和绝对的概念”。(11) 这就是说,奴隶的劳动(不同于主人的享乐)的一个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按照普遍概念铸造事物的力量,因此它是技艺、科学、知性能力和一切普遍形式的真正来源。而当奴隶通过劳动创造了这种“纯粹形式”时,他实际上也获得了主人冒生命危险去争夺的东西,即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讲主人的真理是奴隶,“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作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作的事”。(12) 当然,奴隶的这种自由还只是抽象的观念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奴隶只是在他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看到了自身作为一个普遍自由存在的影像。但是黑格尔认为,将这种抽象的自由变成现实的自由,从而实现真正的“相互承认”的过程,正是进步和解放的本质。
三、马克思论承认的异化与回归
泰勒在其大作《黑格尔》中指出:“奴隶改造的重要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和惩罚性劳动。黑格尔用简短的3页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精神现象学》的最重要段落。因为这些论题不仅对黑格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以不同形式变成了一项漫长的事业。”(13) 这一概括非常正确。尽管不曾发现马克思直接论及《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文本,但黑格尔发明的承认问题却无疑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事业保持着一种本质联系。
《精神现象学》中的承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的重大影响,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中,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解是把承认问题和劳动连接起来。原先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联系并不明显,承认主要是通过冒生命危险的“斗争”来实现,而“劳动”在其直接性上则是在完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被迫接受的奴役。而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则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相互承认的直接形式和主导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劳动是作为全面自由的劳动即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比如在你享受和使用我的劳动产品时,对我来说,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最终说来,这种基于我的自由劳动的相互承认就表现在:“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而这一点是通过“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来实现的。(14) 很显然,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相互承认。
但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关心的主要不是抽象的承认概念,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承认问题。在这个文本中,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承认、尊严和奴役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黑格尔的承认问题增添了全新而且更深刻的内涵和意义。这一批判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如果使用黑格尔的术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生活内容已经不是“斗争”,而是“劳动”;但这不是黑格尔心目中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劳动,而是作为谋生手段和牟利手段的劳动,马克思亦称之为“生产性劳动”。劳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实体,并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规定。随着劳动的彻底异化,承认的意义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按照黑格尔的描述,主人冒生命危险去斗争是为了让自己的荣誉被人承认,这种承认是一个精神性的目标,主人由此证明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人;但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最大化成为核心生活目标,承认本身亦发生异化,其对象不再是荣誉,而是财富和财产权。马克思发现,承认的这种异化基于劳动的异化。随着劳动成为谋生的劳动,生产成为财富的源泉,情况变成了“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劳动的纽带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私利,每个人都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自己私利的对象化,因此,“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15)。马克思指出,承认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的本质是要求被别人承认为人,“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16)。具体来说,当承认从黑格尔所谓两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变成两个物品拥有者之间的关系时,相互承认的问题就变成了:“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对自己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17)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新版本的“为相互承认的斗争”中,黑格尔在原初意义上讨论的奴隶和主人、尊严和荣誉问题均发生了彻底的颠倒和蜕变。在这里,人不再成为别人的人身的奴隶,而是成为自己的物品的奴隶。这就是拜物教形式下的主人/奴隶关系:当你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仅仅看成是攫取我的产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时,“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像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恩赐”。(18) 在马克思看来,与黑格尔描述的那种直接人身意义上的主奴关系相比,现代人“被物品弄得相互奴役的状况”是一种更不幸的奴役状态:“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19) 随着主奴关系转入拜物教形式,人类用来表达相互承认的语言也发生了畸变。马克思对此作了震撼人心的描述:“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20)
对马克思来说,主奴关系的核心无疑就是阶级斗争,承认问题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不止一次讲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现代奴隶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奴隶,这个现代奴隶阶级将通过劳动和斗争使自己获得解放,这和黑格尔曾经描述的几乎一样。马克思深受黑格尔下述观点的影响:奴隶在劳动中因为经受住了事物的坚实性和独立性的抵抗力,从而为所有人的最终解放作好了准备,这表现在马克思的如下说法中:“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1);而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解放自己,就在于“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22)。但和黑格尔有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解放规定为一个现实政治问题,而非思辨哲学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规定,现代无产者通过阶级斗争去追求的承认,不是任何特殊的权力和荣誉,而是最一般的“人的权利”和“人的本质”,这好像和黑格尔那种精神性的承认要求相似,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人的本质和权力”是一个更深刻的社会目标,即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经济领域争得平等。这是一次最彻底的解放,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回归。它是一个最普遍的斗争目标,马克思也把它称为“全人类解放”。这里包含对现代承认问题的本质的一个特别深刻的理解,即现代奴役的实现形式不是主人对奴隶人身的统治,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对劳动者的压制,也就是资本以私有产权资格索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统治和不平等。这就是“经济的政治性”问题。按此理解,马克思提出,现代无产阶级与原来的奴隶不同,它是一个“普遍的阶级”,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工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借用西耶斯描述法国第三等级的名言,把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承认”表达为:“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23)
四、泰勒“承认的政治”:20世纪晚期以来的承认问题
在当代,黑格尔开启的承认问题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也更加政治化。比如施米特提出,政治生活是最基本的生活,而政治问题的核心就是区分敌友。在这一理解中隐含着将承认问题政治化的一种极端趋向: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承认与不承认。施米特认为马克思阐发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这一问题最具历史影响的一个例证,“这一对立面把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对抗归结为与人类最后敌人的最后一战”。从政治问题着眼,施米特高度重视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在关键方面处处保持着政治性”,黑格尔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关注显示了“他那种不允许以‘非政治的’纯粹性或纯粹的非政治性为借口设定精神陷阱的哲学真诚”。因此施米特特别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有在一种政治思维中才能被正确把握。比如他用黑格尔量与质辩证转化的理论对前述马克思关于“经济的政治性”命题作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解读:“当经济财产达到了特定的量,就会变成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权力,财产变成了权力,最初纯粹由经济激发的阶级对立变成了敌对阵营的阶级斗争。”(24)
20世纪对黑格尔承认论题的一次更重要的理论回应,是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20世纪晚期,在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所谓“文化多元主义”,即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承认的要求,成为西方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泰勒以其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发表了重要论文《承认的政治》,重新解读承认问题,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泰勒的研究首先区分了承认和认同:所谓“认同”表示一个人对自己是谁以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而“承认”的问题则在于:我们的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泰勒据此提出,承认是人类的一种重大需要,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对人造成伤害,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25)。
泰勒对承认的研究以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为起点,指出最初对承认的要求指向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荣誉观念,此种荣誉与不平等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它要求的是别人不能享有的“优先权”。随着旧的等级制度和传统荣誉观念的崩溃,现代的尊严概念成为承认的核心诉求,它的基本前提是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因此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承认。以这个现代尊严概念为基础的平等承认的政治,就是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根据泰勒的研究,18世纪末产生了关于个人认同的全新理解,强调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本原就在于他自身,即“把自己看作是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自我观念的产生,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转向的一部分。卢梭关于道德的问题应听从我们自己内在天性的声音的主张,是这种现代个人认同的代表性看法。但泰勒强调,即使这种现代自我认同的建构,也必须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实现,而且更加依赖于他人的承认。因为与前现代社会相比,那时的认同由身份和等级决定,因此内在地包含着普遍的承认。“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并不谈论认同和承认,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我们那样的主题化。”而在现代社会,“内在发生的、个人的和独特的认同却不先验地享有这种承认,它必须通过交往来赢得承认”(26)。按照泰勒的分析,这种现代承认的主题化在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特别突出地表现为“平等尊严的政治”与“差异的政治”之间的分歧:平等尊严的政治强调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个人权利,不允许有任何例外,这就是作为欧美国家宪章主导原则的权利自由主义;差异的政治则认为应当承认个人或群体的独特的认同,正是这种独特性经常被占统治地位的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和同化。从差异政治的观点看,平等尊严政治所采取的无视差异的价值中立化原则,表面公正,实质则是傲慢的和高度歧视性的,尽管这种傲慢和歧视以温和方式来表现。
很显然,差异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承认问题,即要求尊重每一个他者的价值,泰勒“承认的政治”最有批判性的内容正是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分析。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假设,即自由主义可以提供一个价值中立的基础,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交往和共存。对此,泰勒指出:“自由主义并不能为所有的文化提供可能的交往基础,它只是某一种文化的政治表述,与其他文化是完全不相容的。”(27) 在文化多元化和相互渗透愈演愈烈的今天,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核心要求仍然是黑格尔提出的相互承认,即:不仅应当允许世界上所有不同文化继续存在,而且应当承认所有不同文化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为此泰勒引用了弗朗兹·法农的著名观点:西方殖民者给殖民地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他们强加于被征服者的一种贬抑性的自我形象;而法农主张的承认要求就在于:“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群体通过向被征服者反复灌输他们的低贱形象来巩固其霸权,所以,改变这种低贱形象是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必由之路。”(28) 这几乎是重新回到黑格尔的观点:真正需要的承认是通过斗争得到的真正的尊重。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承认的主题化正是在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中得到最早也最有影响的阐述。按他的解读,正是黑格尔让我们知道,人只有在得到承认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地成长,寻求承认并不意味着缺乏美德;基于等级制的旧荣誉观的错误就在于,它无法解释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斗争中的失败者固然得不到承认,但胜利者同样得不到,因为他们赢得的只是失败者的承认,这种承认缺乏意义。泰勒认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必将导向一种平等尊严的政治:“寻求承认的斗争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这就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继卢梭之后,黑格尔在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中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在那里,‘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29)
【注释】
①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5、216—218页。
②③④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2—124页。
⑥同上书,第127页。
⑦同上书,第129页。
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⑨⑩(11)(12)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第129—132页。
(13)泰勒:《黑格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14)(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7页。
(15)(16)(17)同上书,第34、24—25、35页。
(19)(20)同上书,第19、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4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3页。
(24)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07、154、141页。
(25)(26)(27)(28)(29)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291、298—299、320—321、323—324、310—311页。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zx/2014-02-21/24915.html-红色文化网